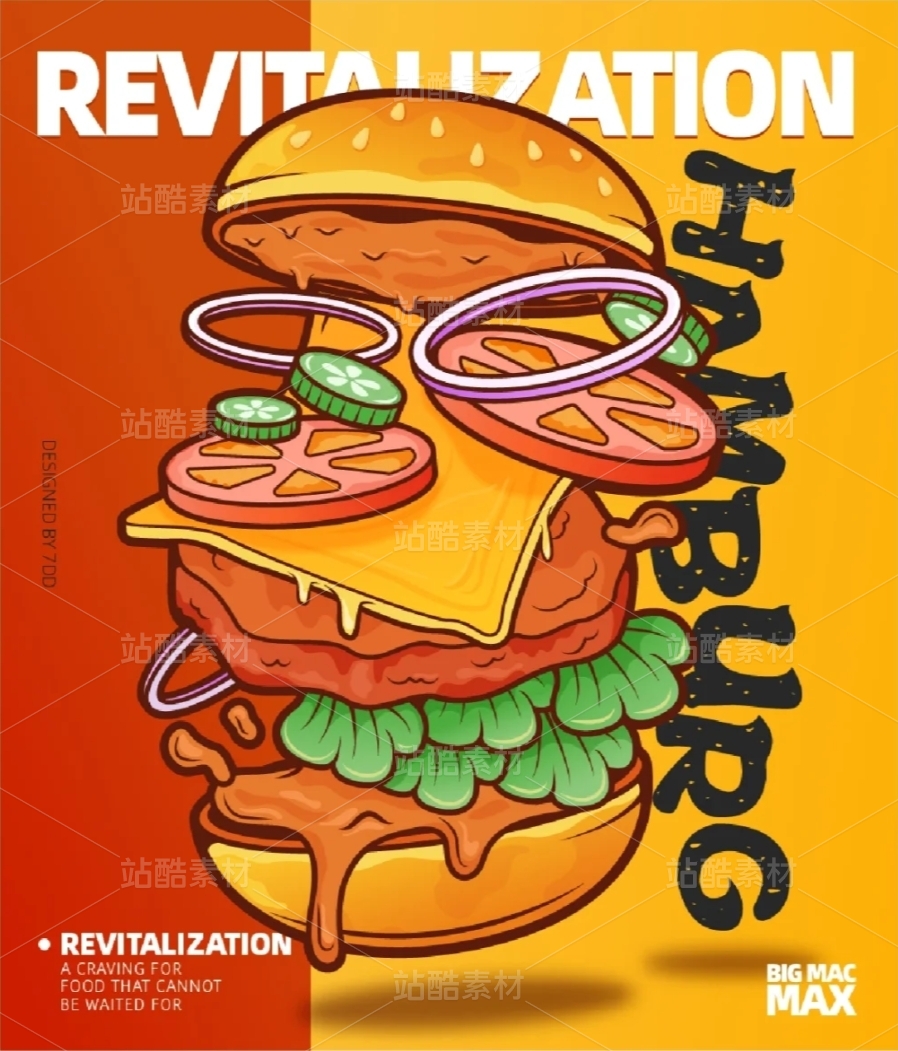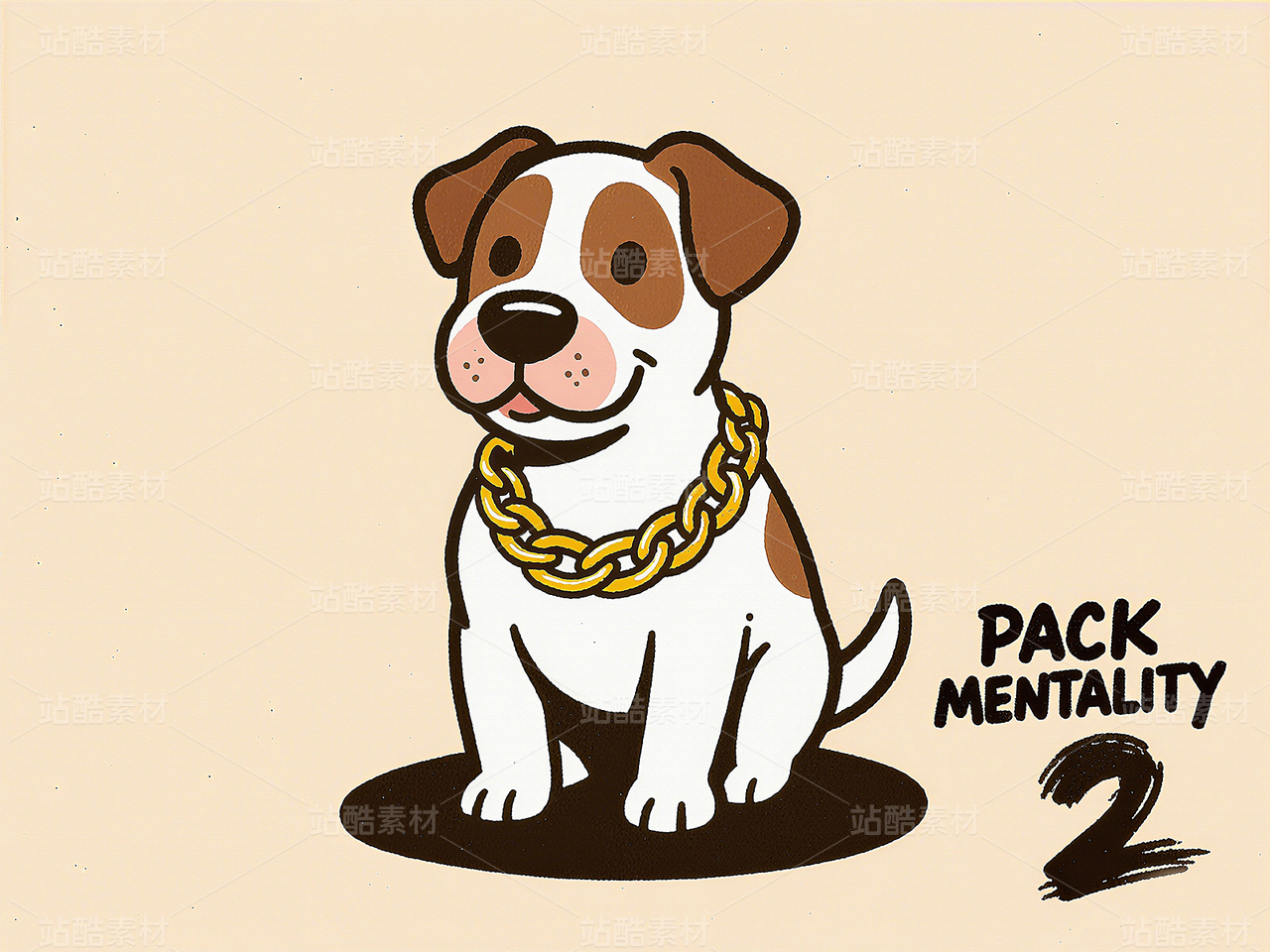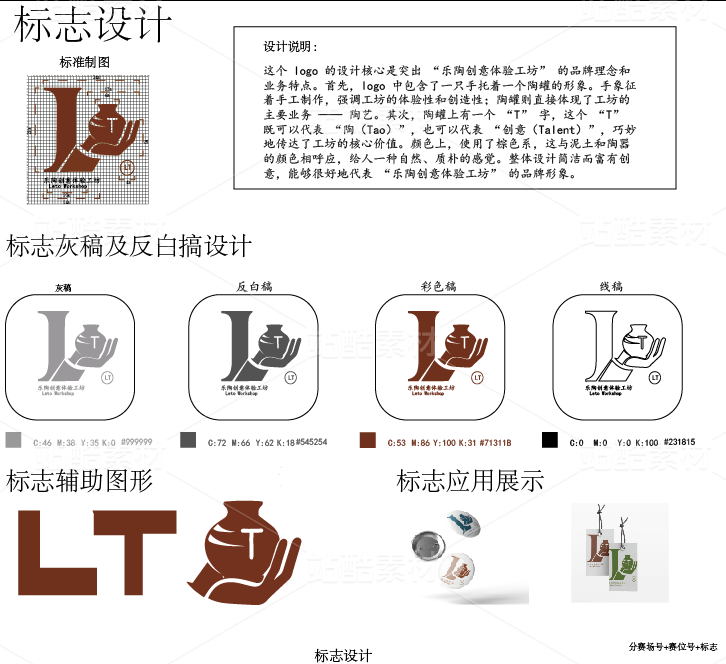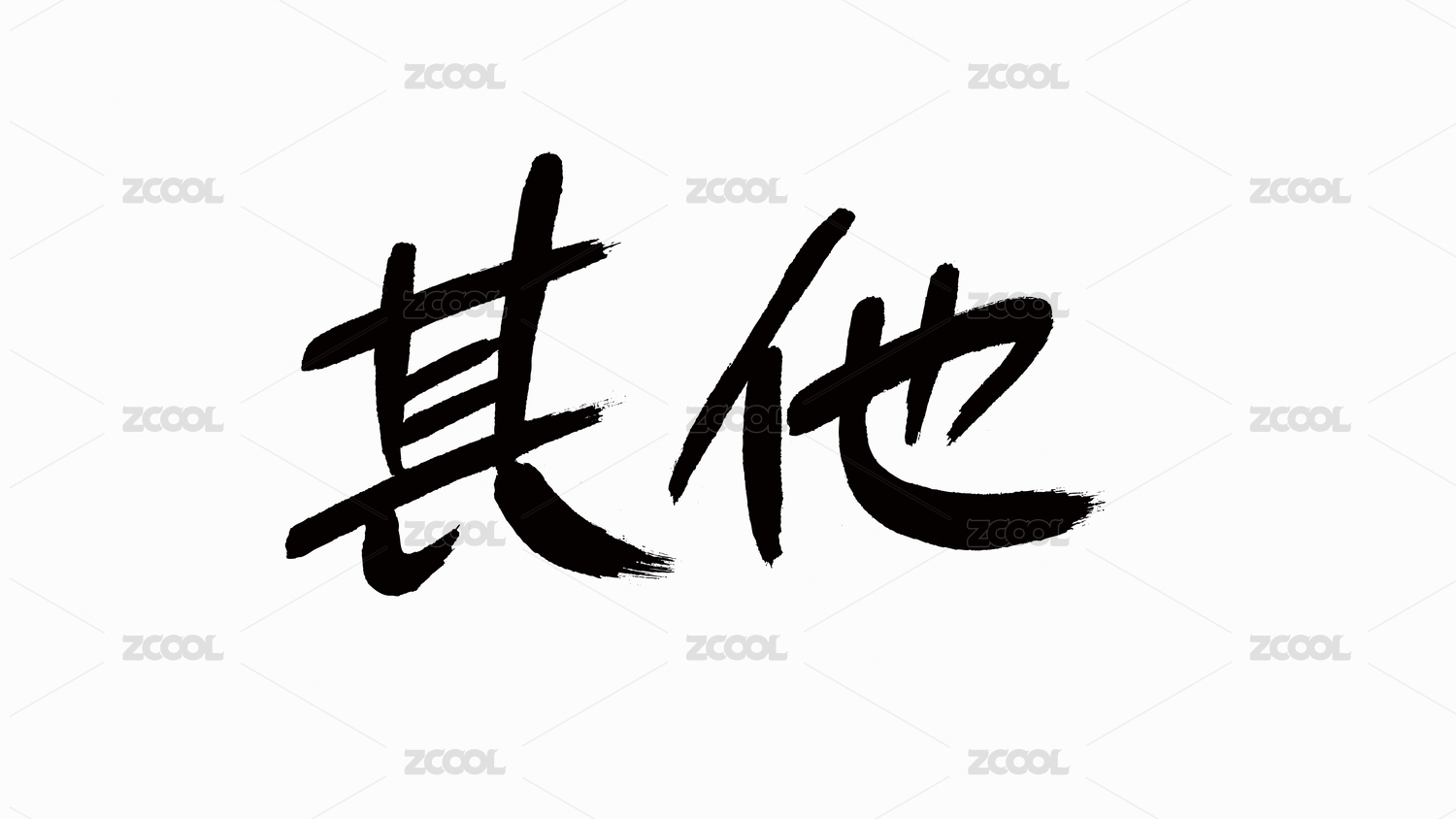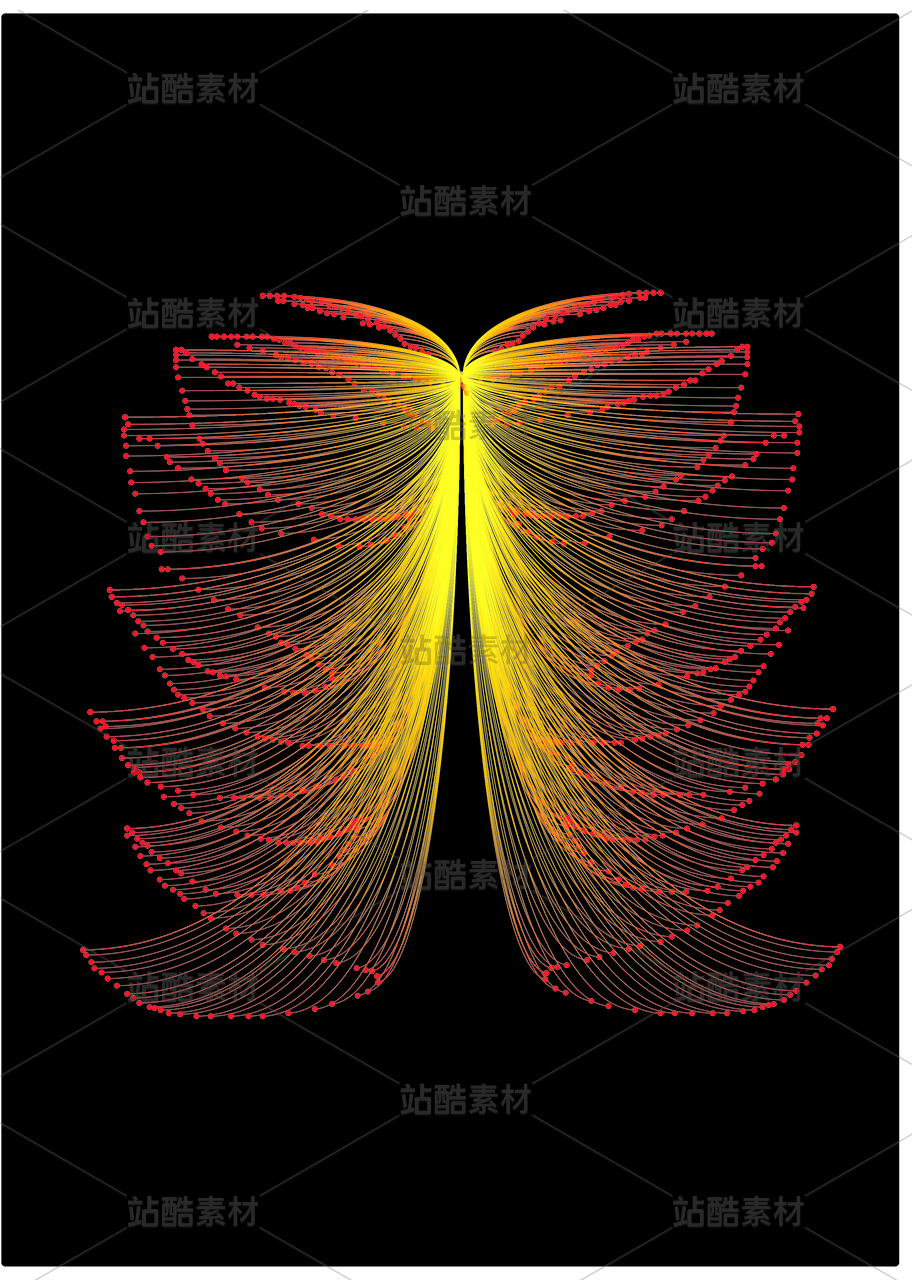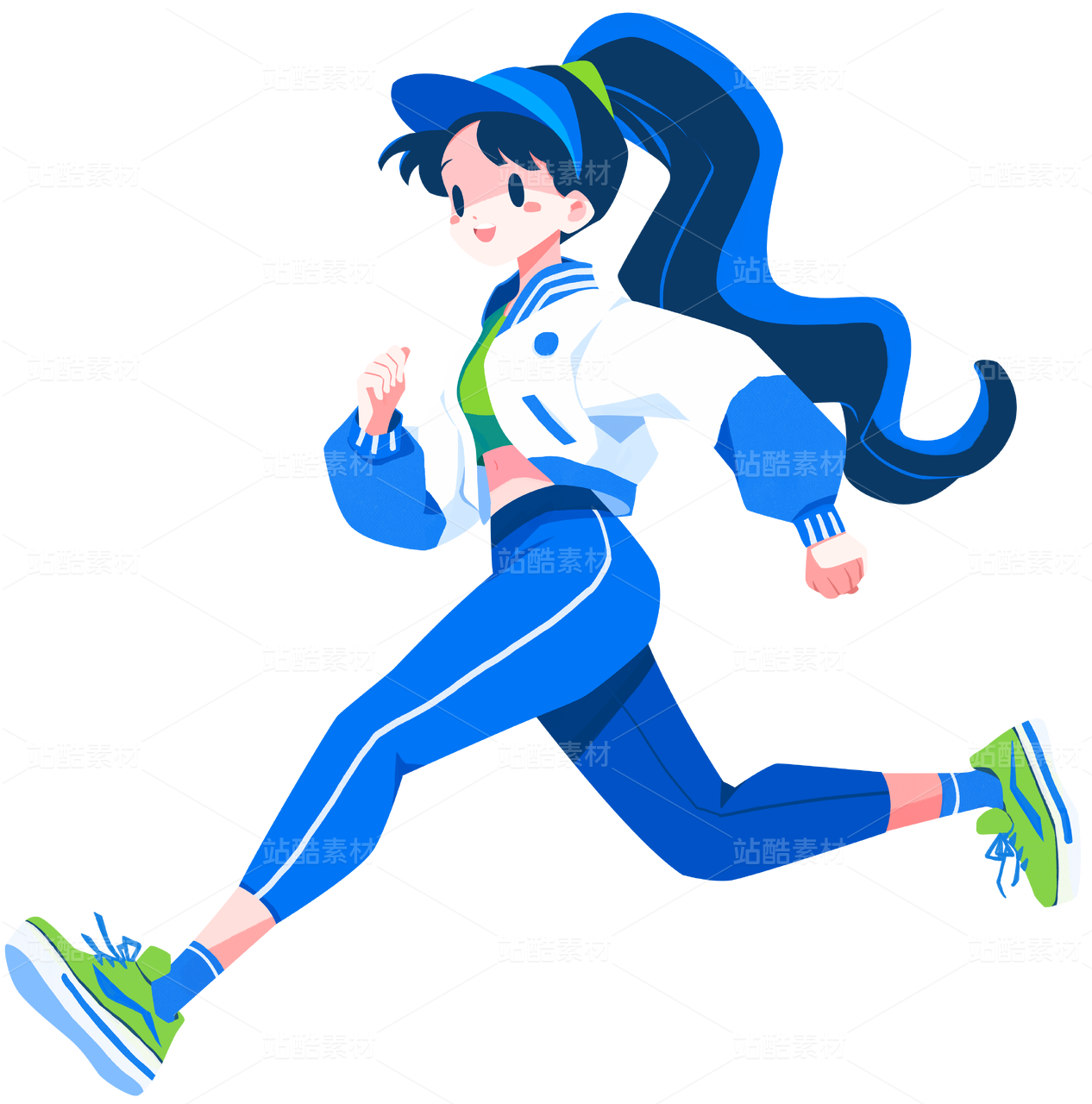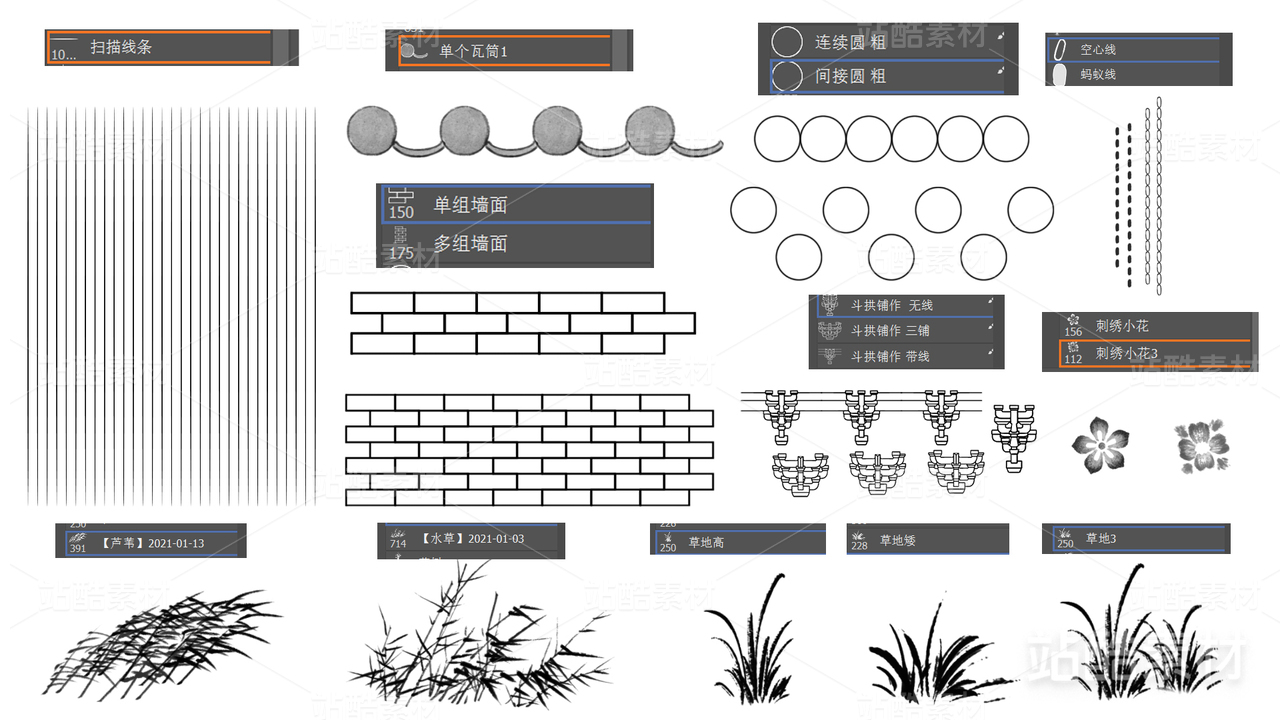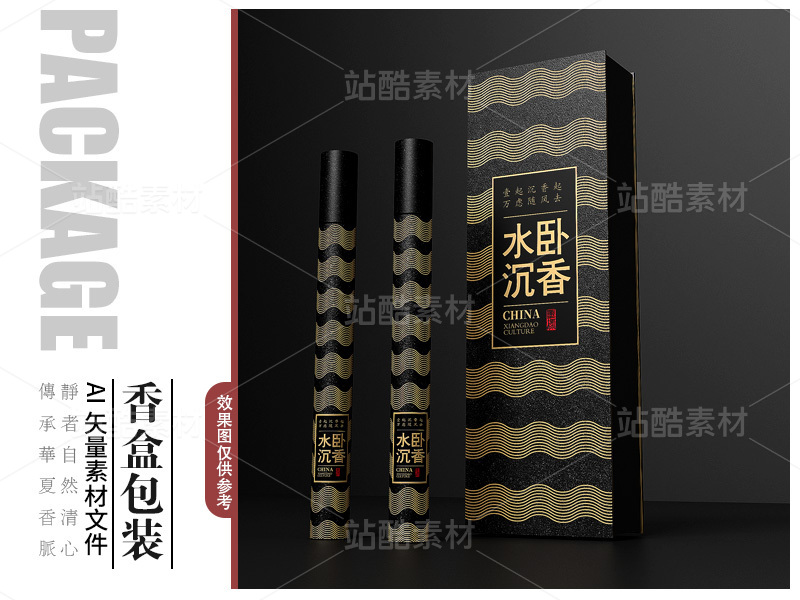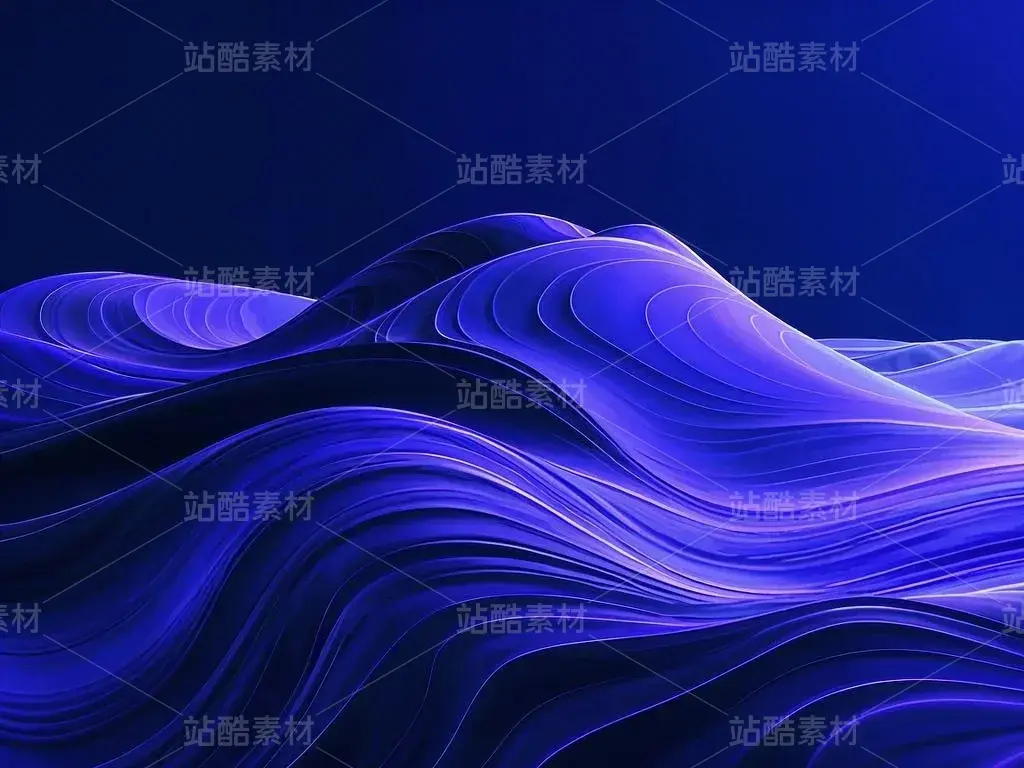何谓色彩美学?何谓色彩通识?何谓中国颜色?(二)
温州/平面设计师/1年前/1025浏览
版权
何谓色彩美学?何谓色彩通识?何谓中国颜色?(二)
中国传统颜色讲解(仅供参考)黄色
半见色(浅黄色)
半见,出自西汉学者史游编辑的识字和通识课本《急就篇》,原文是:
“郁金半见缃白韵,缥缤绿纨皂紫诞。”
唐代学者颜师古注释说:
“半见,言在黄白之间,其色半出,不全成也。”
半见是隐约可见的浅黄色。
《急就篇》里不少颜色词,
“郁金半见缃白齁,缥绿纨皂紫碾。蒸栗绢绺缙红燃,青绮绫縠靡润鲜”。
这其中郁金、半见、缃、白、缥、、绿、皂紫、蒸栗、绢、绀、缙、红、然,都是单独的颜色。
半见的色相来自春天的柳色,唐代官员张季略写过一首《小苑春望宫池柳色》:
“韶光归汉苑,柳色发春城。半见离官出,才分远水明。青葱当淑景,隐映媚新晴。积翠烟初合,微黄叶未生。迎春看尚嫩,照日见先荣。傥得辞幽谷,高枝寄一名。”
树上隐约可见的柳色,不能遮挡离官;池边隐约可见的柳色,提醒池水的存在。春天的柳叶还没长出来,阳光照过来,如烟、微黄的柳色正是隐隐闪闪的半见色。
看池边春柳是唐代人的习惯,相同题目的《小苑春望宫池柳色》颇有几首,其中的句子可以看到半见色的痕迹:
“风从垂处度,烟就望中生”(元友直);“濯濯方含色,依依若有情”(沈回);“影宜宫雪曙,色带禁烟晴”(张昔);“嫩叶随风散,浮光向日明”(崔绩);“光含烟色远,影透水文清”(杨系)。
黄白游,讲的是颜色,似乎又不是颜色,这正是中国传统色的微妙之处颜色可以来自天地万物的具象,也可以来自人类心灵的意象。之所以选择黄白游作为一种色名,因为它兼具了具象和意象两重美感。
写《牡丹亭》的明代文人汤显祖,文采斐然,章句拔群,然而仕途不顺。友人吴序劝汤显祖到徽州去晋见退休在家的宰相老师许国,汤显祖却写了一首《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微州。”
黄白,既是具象的黄山、白岳(齐云山),也是意象的神仙梦;既是具象的黄金、白银,也是意象的富贵梦。友人说的对:去徽州见见你的老师许国,黄白之间,气象万千,富贵袭人。在汤显祖的心里,徽州的黄白已经不是神仙梦、富贵梦,而是他一生无法抵达的世俗之气,他选择了放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请原谅我一生痴绝,不去徽州也罢,我这一生,既没有神仙梦,也没有富贵梦。
汤显祖之后,我们不但把黄白游看作黄、白中间的颜色,还看成我们挥之不去的神仙梦、富贵梦。
绢纨,出自西汉学者史游编辑的识字和通识课本《急就篇》,原文是:
“郁金半见缃白齁,缥缤绿纨皂紫诞。蒸栗绢绀缙红继,青绮续靡润鲜。”
东汉学者张揖在《广雅》里注释说:“
绡谓之绢,谓之红,缰谓之终,缁谓之皂。”
绢纨,等同于绡纨,绢和绡同指未经染色的丝织品。
优质蚕丝的天然颜色为乳白色略黄,这种色相近乎白,微带黄,于是,绢和绡是什么颜色就分成两派说法:一派以唐代学者颜师古和清代学者王念孙为代表,他们认为就是白的,所以他们称“绢就是未经染色的白色丝织品”;另一派以东汉学者许慎为代表,他在《说文解字》中说“绢,缯如麦”,也就是他称“绢就是未经染色的麦稍色丝织品”
麦稍色为何种颜色?麦稍就是麦茎,麦茎在不同成长时期颜色亦不相同:初长之时为青色,成熟之后为黄色。清代学者段玉裁在注解《说文解字》时就认为:
“缯色如麦茎,青色也。”
显然他认为麦秱色是青色,也就是绿色。
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地出土木褐载:
“紫丸(纨)上衣五,绿丸()上衣十,绢丸(纨)上衣四,□丸(纨)上衣二。”
紫纨、绿纨、绢同列、而纨既已说明其材质,紫、绿、绢应是三种不同的颜色。既然如此,绢(也就是麦稍色)还应该是绿色吗?
在考证汉帛的基础上,当代文物学者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指出:
“在汉代,绢特指未漂涑的泛黄色之帛。”
可以推断,绢纨色或者麦色是成熟麦茎的浅黄色。
所谓未经染色的白色丝织品,古文中以缟或素来专门表示。颜师古和王念孙认为绢是白色也并不是杜撰,因为优质蚕丝的略黄颜色并不如麦茎的浅黄那么明显,而是一种不透明的乳白色略黄。明末清初诗人王又旦写云气的乳白色:“金庭郁参差,云气张绡纨。”绡纨和绢纨是一回事无独有偶,清代文人恽敬在《游庐山后记》中形容庐山云海的乳白色,也用到三处“绡纨”和'绡纨色”:“视前后人,在绡纨中”
“岩上俯视石峰苍碧,自下矗立,云拥之,忽拥起至岩上尽天地为绡纨色,五尺之外,无他物可见”“已尽卷去,日融融然,乃复合为绡纨色,不可辨矣”
松花,作为一种色名,至少上溯到唐朝。如果不去考据松花的实物具象、它的颜色是扑朔迷离的:在网上查到的松花色,有黄中带绿的,还有浅绿色的。
松花可不是松果,它是松树雄枝春天抽新芽时的花骨朵。我在查证松花色时,遇到擅用松花粉做滋补品的专家,她说:
“抖落的松花粉像婴儿肤色一样娇嫩。”
然后,看到松花的实物,具象是最有说服力的,松花是黄色。
唐人为松花色所倾倒,
“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苔锦含碧滋”“自看和酿一依方,缘看松花色较黄”
分别是唐代诗人李白和王建的名句。松花色的纸,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传统色衍生品,所谓薛涛松花。薛涛之后,制作彩色笺纸成为雅事,明代戏曲家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说:
“蜡砑五色笺,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罗纹笺为佳,余色不入清赏。”
唐代诗人元稹在松花笺上回应薛涛的知音情意:
“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卓文君和薛涛都是在川地生活的女子,都是敢爱的,她们的爱就像滑腻的锦江水、娟秀的峨眉峰。
爱是滋补品,松花粉也是滋补品。抖落松花粉,古人专用一个“拂”字仙气得很。松花粉可以做松花酒,也可以做松花点心,据说食之身如燕、颜如春。北宋文人苏轼写过广告语:
“一斤松花不可少,八两蒲黄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钱,两斤白蜜一起捣。吃也好,浴也好,红白容颜直到老。”
缃是浅黄色,缃叶是桑叶初生的颜色,但也用来说荷叶的颜色,
“鱼戏排缃叶,龟浮见绿池。”
缃和缥一样,是中国传统色的重要色名。缃缥、缥缃是读书人指代书卷的专用词,因为古人习惯用浅黄色或淡青色的丝帛做书衣、书囊,所以捧着书的、拎着书的读书人是与这两种颜色为伍的。主持编辑《文选》的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是热爱文学和佛法的大才子,他在《文选》的序中说:
“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
西晋文人张华的《博物志》中写到一种变色虫,这种虫子
“视之无定色,在阴地色多缃绿,出日光中变易,或青或绿,或丹或黄,或红或赤”
。绿是浅黄绿色,这种像白石英的一寸虫,在阴凉地看是浅黄绿色的,到了阳光下颜色就变成了蓝、绿、鲜红、黄、浅红、正红,当时的女子拿它做首饰,蛮奇幻的。
初生的浅黄色桑叶是缃叶,荷叶怎么也称作缃叶呢?夏日池塘荷叶青青,转眼就到了秋天,元末明初诗人刘松想告诉青年男女青春易逝,他说
:“荷叶黄,荷叶青,四月五月风日清。荷叶青,荷叶黄,八月九月秋风凉。越湖女儿颜似玉,隔船窥郎心眼熟。赤尾鲤鱼花下游,白头鸳鸯露中宿。欢会苦乖绝岁月同飞扬。王母不西游,娥眉刷秋霜。少年之乐乐未央,莫遣老大徒悲伤独不见,荷叶黄。”
栀子,其果实含有栀子昔,这是一种天然黄色素,自古以亲就是染黄的染料。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讲过一句著名的话:
“有千言卮(通栀 )、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家里有千亩可以生产黄色染料的栀子、可以生产红色染料的茜草,这人就是可以笑傲千户候的富豪。
古代的日本也使用栀子染黄,所以日本传统色里也有栀子色,和歌里有这么一段:
“思君与恋君,一切都不说。但将身上衣,染成子色。”
栀子果实对人类非常有用,不仅可以用于衣物染色,还可以用于食品染色,甚至可以作为中药。各种药典里记载,栀子果实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这样的好东西实在难得,杜甫对此感慨赋诗: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
“与道气相和”亦作“与道气伤和”,其解释是栀子果实“性极冷”,伤胃,从上下文看,“气相和”比“气伤和”更通顺。如此美好的植物是上天的馈赠,所以杜甫将栀子树作为庭院树,“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经霜看果实透红,过雨看叶子深绿。
嫩鹅黄,唐宋年间优质发酵酒的颜色。古代以秣米酿酒,各家有各家的招儿,制曲和酿造工艺差别大,酒的质量差别也大,酒色是辨别酒质的重要依据,一般说来,绿色酒比较多见,黄色酒好于绿色酒,琥珀色的酒接近于现代黄酒品质,红色酒稀罕惹人喜爱。
最早把鹅黄跟黄色酒挂钩的是唐代诗人杜甫,他说: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鹅黄诗此起彼伏,鹅黄随即成为黄色酒的代名词。
嫩鹅黄,也是唐代诗僧寒山的色彩体验,他在诗里写下这种颜色的衣服
:“衫作嫩鹅黄,容仪画相似。常骑踏雪马,拂拂红尘起。”
北宋文宗黄庭坚他写酒写茶都离不开嫩鹅黄,
“浮蛆拨官醅,倾壶嫩鹅黄”“已醺浮蚁嫩鹅黄。想见翻成雪浪”
其实,过滤未尽的浊酒也会出现黄色酒,但那是一种浑浊的黄,不似嫩鹅黄,嫩鹅黄是黄酒曲酿出的清酒,独有的亮色容易分辨。过滤得好,去糟取清,则是清酒,清酒有三大特点:酿造时用曲量大、选料精细、发酵期长。这种酒成熟后酒液清澈,故谓之清酒。
“一杯浊酒喜相逢”,“金樽清酒斗十千”浊酒与清酒,是两种心境、两种境遇。
雌黄,中国画颜料,柠黄色,化学成分是三硫化二砷。雌黄与雄黄是共生的,宛如矿石鸳鸯,从矿石开采出来的雌黄是像云母般的软质、易碎、片状晶体,俗称“四两雌黄,千层金片”。在矿石中存留的雌黄遇到空气会变硬,就成为石黄,正黄色,化学成分还是三硫化二砷。
古人用黄纸写字,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改。西晋名士王衍喜好玄学,与人议论老子、庄子,经常有漏洞,前后矛盾,别人指出来,他也不在乎,顺口改一个说法,被人称为“口中雌黄”,后来就有了“信口雌黄”的成语。
北宋文理双全的沈括写《梦溪笔谈》,其中记载: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
涂涂改改,雌黄是万能灵药。
顺便说一下雌黄的伴侣,雄黄,橘黄色,化学成分是四硫化四砷,氧化后生成三氧化二砷,即砒霜。
黄河琉璃,出自明代诗人纪坤的《渡黄河作》:
“黄河天上来,其源吾不知。东南会大海,吾亦未见之。但观孟津口,汹涌已若斯。放眼三十里,日耀黄琉璃。”
日光照耀下的黄河水,如同黄琉璃,故取此色名。
日光、黄河,都有母性光辉的意象,日光照耀黄河水的具象,因为诗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升华,黄河琉璃透射出的是丰饶的力量。从具象到意象的升华,不仅存在于世俗世界,也存在于信仰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有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
,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史书名是《格鲁派教史黄琉璃》。
竹席因为色黄而有光泽,也曾被称为黄琉璃,唐代诗人韩愈的
“携来当昼不得卧,一府传看黄琉璃”
,宋代诗人苏轼的“皇天何时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都看得出诗里那一方凉意。
故宫的色彩体系,最明亮的是黄琉璃瓦和红墙的大面积视觉效果,这种美学是被我们接受的,我们接受的前提是故官的历史地位背书了这种撞击的配色,这同样是具象升华到意象的色彩审美。
黄不老,就是黄檗,其树皮是黄色染料。黄不老是黄檗的音转,“不老”读作一个音,这个典故出自元代散曲家刘时中的套曲:“
剥榆树餐,挑野菜尝吃黄不老胜如熊掌,蕨根粉以代糇粮。”
黄檗树皮可以清热泻火,味道虽是苦的,饥荒年景却也是宝贵食物。黄檗的苦,古代人是尝够了,留下不少古诗:
“黄檗郁成林,当奈苦心多”(《子夜歌》);“哑子谩尝黄檗味,难将苦口对人言”(《京本通俗小说》)。
同栀子一样,黄檗染黄的历史悠久,南北朝文人鲍照写过“锉染黄丝”表明当时用黄檗染丝线是很盛行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颜色对照的色谱,文字记载的颜色很难确定具体的色值,所以我在确定栀子和黄檗的颜色时,也看了日本传统色的色谱,日本的栀子色是栀子加了一点点茜草染出来的,颜色是黄里带一点点红,日本的黄檗色是深黄色偏绿,而《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的黄不老定为栀子果实原本的土黄色
我看到栀子和黄檗的染色过程,二者染出的颜色均以深浅不一的黄绿色为主,这是文字考据与染色实践的互证。
秋香,香色的秋天版。先说香色,香色是往黄色里添加绿色,从而增加了黄色的雅致感,可能是从缃色演化而来的,缃是桑叶初生的浅黄色,香与缃同音,借用之,以俗字代生字。再说秋香色,秋意浓,色深沉,秋香是浓郁一些的黄绿色。
香色曾是清代初期皇太子的服色,清代宗室昭梿的《啸亭续录》说:
“国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后储位久虚,渐忘其制。近日庶民习用香色,至于车帏巾悦无不滥用,有司初无禁遇者,亦未习典故故也。”
因为清代后来不立太子,香色的禁忌就被忘了,民间习而滥用。
香色和秋香色在清代本是禁色,在《清史稿·舆服志》有载:
“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色、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
《红楼梦》里众人轮番穿着秋香色的服饰,第三回有
“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
(王夫人 ),第八回有
“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
( 贾宝玉),第四十九回有
“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裉小袖掩襟银鼠短袄”
(史湘云),第一百零九回有“秋香色的丝绦”(妙玉)。
最厉害的是第四十回,贾母教导王熙凤换窗纱:
“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地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
贾母轻描淡写,家财万贯的气派在见多识广的话里藏着。
蒸栗,黄色如蒸熟的栗子。出自西汉学者史游编辑的识字和通识课本《急就篇》,书中记叙了不少颜色词,原文是:“蒸果绢绀缙红织,青绮绫教靡润鲜。”东汉文人王逸《玉论》总结玉的颜色:
“赤如鸡冠,黄如蒸栗,自如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
黄玉如同蒸果色。
以栗形容玉,始于孔子。子贡向孔子问道:为什么有道德的人以玉为贵而不重视好看的石头?孔子回答说: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判,行也:折而不,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
孔子说玉有七种好处,如君子有七种德行,在形容玉缜密而有文理时,孔子说像果,这里说的栗是栗木,这种木材确实缜密而有文理。作为栗木的果实,栗子从此就与玉结下不解之缘。
明代戏曲家高濂写《遵生八笺》,论古玉器:
“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以黄为中色,且不易得,以白为偏色,时亦有之故耳。今人贱黄而贵白,以见少也。然甘黄如蒸栗色佳,焦黄为下。”
甘黄就是蒸栗色,这是古玉之上品。
清代文人陈性写《玉纪》:
“有受黄土沁者,其色黄,色如蒸栗,名曰黄。若受松香沁者,色更深,复原时酷似黄蜡,谓之老黄。”
陈性是晚清奇人,断古玉如神,他说古玉受黄土的沁色,蒸栗色,叫黄;古玉受松香的沁色,黄蜡色,叫老坩黄。《遵生八笺》中的甘黄色,源头是黄色,就是蒸栗色的玉。
按照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和田玉鉴定与分类》(GB/T 38821-2020),玉色分为白玉、青玉、青白玉、碧玉、黄玉、糖玉、墨玉、翠青玉八大类,蒸栗当归于黄玉色。
杏黄,杏子微微发红的黄色。清代戏曲家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说:
“杏黄、江黄即丹黄,亦曰缇,为古兵服。”
《通雅》讲:“丹黄曰缇。”缇就是发红的黄色,丹黄、杏黄、江黄都是这个颜色,江黄疑似是委黄的误笔,古代军服是丹黄色。
发红的黄色,如果红不多,则是杏黄;如果红更多一些,则是金去,金在清代官方被称作金黄。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的《凤仙谱》中描迷金去的颜色是:
“杏黄带浅红,乃赭、朱二色和合而成。”
杏黄、金黄,在清代都是皇家标识色,杏黄为太子所用,金黄为皇子所用。
清代《皇朝礼器图式》记载:
“皇太子龙袍色用杏黄”“皇太子妃龙袍色用杏黄”“皇太子端罩黑狐为之杏黄缎里”“皇太子冬朝服色用杏黄披领”“皇大子夏朝服色用杏黄披领”“皇太子妃冬朝袍色用杏黄”“皇太子妃夏朝袍色用杏黄”
事实上,清代康熙朝之后很少设立皇太子。因杏黄色在典制中的特殊地位,杏黄色舆服往往用于思赏重臣,笼络亲近,比较少见的是杏黄轿,多见的是杏黄伞、杏黄辔。清代《钦定八旗通志》记载“(杏黄伞)止许京城外用!京城内不许排列。
清代以前,杏黄色除了军服,也是民间常用色彩,并无禁忌。北宋文学家秦观咏:
“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
清代文学家毛奇龄咏!“旧院双扉樊素宅,新歌一曲杏黄衫。
即使在清代,早年和后期个别情况下,“杏黄衫子”也有咏颂:
“纨扇轻裁蛱蝶罗,杏黄衫子晚晴多,卷帘双燕引新雏”(李雯);“杏黄衫子藕丝裙。谁作伴,自成群”(邹祗谟);“选胜青郊暂作欢,杏黄衫子试轻纨”(汪由敦)。
明黄,升上中天的太阳色。《明史·奥服志》记载:
“天顺二年(1458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
早在明英宗年间,明黄就被确定为皇家标识色。此后,明孝宗上再次明确:“玄、黄、紫、皂乃属正禁,即柳黄、明黄、姜黄诸色,亦应禁之。明黄不是在清代才成为禁色,早在明代就是了。
到了清代,《皇清开国方略》记载:
“(天聪六年,1632年)甲子朔,布令国中,以是月二十日为始,黑狐防、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等服非上赐不得用。”
皇太极重申了明黄为禁色,但当时还没有定为皇帝专用。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富察氏驾崩,乾隆帝深为哀恸,
“列后衾褥用明黄织金五采九凤缎”,“凡七层金棺套用明黄行龙妆缎”,葬仪规格之高可见一斑。同年,乾隆帝封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皇贵妃仪仗内车舆,例用明黄帷、金黄,今请加崇均用明黄”。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书面上,明黄正式成为皇帝专用标识色《清史稿·舆服志》记载:
“(皇帝)朝服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白。”
9
Report
声明
10
Share
相关推荐
in to comment
Add emoji
喜欢TA的作品吗?喜欢就快来夸夸TA吧!
You may like
相关收藏夹
Log in
9Log in and synchronize recommended records
10Log in and add to My Favorites
评论Log in and comment your thoughts
分享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