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其他历史悠久、名头响亮的非遗文化,武侯面塑是一门非常年轻的非遗手艺,它在2020年才被选入武侯区的非遗名录,成为区级的非遗文化。其实从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武侯面塑最大的地域特色——武侯,三国元素的注入让这一地区的面塑创作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动素材,事实上,这也是武侯面塑成为区级非遗文化的重要原因。
翻阅武侯区志,我们发现,在清末之时“面塑”这一走街串巷的小玩意儿就已经流行于武侯大地,此后千变万化,逐渐演变成具有浓厚地区特色的“武侯面塑”。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武侯文化的滋润,才使武侯面塑从一颗嫩芽开出别具特色的艺术之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项经过武侯文化浸润出的民间艺术也同样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每一代武侯区人民心中埋下一颗颗有关武侯文化的种子。红脸的关羽和黑脸的张飞,羽扇纶巾手持摇扇的诸葛丞相,桃园三结义、草船借箭、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鲜明的形象从手艺人的手中雕刻而出,被浓缩于小小的尚未成型的面团之间,随着手艺人的吆喝和脚步走过大街小巷,再流转到孩童的手中为他们带来欢笑,成为他们心中最初的“武侯印象”。武侯文化成就武侯面塑,武侯面塑又雕刻新的武侯文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传统手工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困境是,他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他们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在逐渐消亡。走上那些地名熟悉的街巷和建筑“锦里”、“春熙路”、“宽窄巷子”……这些地名无一不彰显它们各自的来历和历史,然而时间洪流滚滚而过,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和物都改头换面。高大的商业楼节次鳞比、各大商场的灯光彻夜不休、游客来来往往、汽车永不停歇,这些处于黄金地带的街道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走在潮流的最前沿。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人和物的变化只是时代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无须苛责。然而新文化的崛起必然会让一些旧景象消失,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只能从被政府保护起来的建筑之中窥见老成都人民的生活一角,包括那些曾经活跃在街头巷尾的民间艺术,取代它们的,是新时代所滋养的新兴文化。
那么,曾经蓬勃发展的民间手艺只能存活在博物馆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一不在为跟上时代脚步,重新扎根于新时代而付出努力。有的是和时下热播的电视电影等文艺作品相结合,比如即将播出的网剧《狐妖小红娘》就曾经借助其“运用了六种非遗文化”的噱头来打造舆论,有的是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力图在流量时代打造出独特的非遗“IP”,较为成功的有峨眉武术传承人,仅在一家短视频平台中粉丝就破千万,当然,更多的是改换非遗内容,重新取材于流行文化,以非遗技艺为载体,乘流行文化之东风。然而非遗传承众多,真正能够在赛博空间中引起人们注意者绝不是大多数,能够掀起水花的更多的是那些早已声名远扬的非遗手艺,或者是传承人中有青年佼佼者的大力宣传。然而,这样的传承人不可多得,更多的非遗传承历经数代,传承人步入老年,无法熟练利用新媒体宣传非遗,陷入“后继无人”的窘境。那么这些曾经仅是在某个地区或某个时代散发勃勃生机,受众狭小、散若星子的地区特色非遗文化真的最终只能在文化浪潮中逐渐消泯吗?
不是。这次走访武侯,探访武侯面塑区级传承人任芝洪老师,我们惊异地发现,武侯面塑正在以另一种不同于沿街叫卖的方式重新流进新一代武侯人民的心底,在他们心中留下武侯的记忆。
任老师常常辗转于成都各地,有时在武侯,有时在青白江,有时在德阳,有时在简阳,于他而言,坐地铁从首站坐到终点站是常态,通勤通一两个小时并不算太久,而他辗转多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学。上午在文化馆教小朋友捏关羽,下午就可能在老年大学教爷爷奶奶捏孙悟空。多年前在青白江区的一次会议上,任老师受到区领导的授课邀请,欣然同意,就一直教授到今天。以社区文化馆为始,参与诸如“非遗进校园”的社区活动,牢牢以社区为阵地,让面塑从街头走向课堂,这是武侯面塑这一地方非遗面对新兴文化的挤压所走出的新路径。事实上,我们曾一度怀疑过这种上课-听讲的方式真的能让这些七八岁的孩子们打心底里喜欢面塑这门手艺,喜欢三国的这些人物吗?李依然小朋友今年八岁,这段时间她每周六上午都会来到任老师的课堂捏面人,今天她捏了一个关羽的身子,得到了任老师的夸奖。在我们和她交谈时,她显然有些羞涩,除了年龄,她什么都不好意思说,但在我们问她“喜不喜欢你捏的关羽呀?”时,她冲我们点了点头。“大家只是缺少接触武侯面塑的机会,其实武侯面塑上手快,时间短,老年人和小朋友都很喜欢。”任芝洪老师告诉我们。
除此之外,任芝洪老师在青白江区残疾人创新创业基地也开设了课堂,教残疾人塑造面人。不同于教小朋友和老年人,这个课堂更多倾向于职业化训练,为的是给残疾人同胞教授一门赚钱养家的本事。“我有很多学生都在很多比赛中获了大奖,做出的作品也卖了不少,然后我学生的手艺过了我这关,我就会让他们去到我在锦里开设的固定摊位,这样就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任老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道。
在新时代背景下,武侯文化哺育出的武侯面塑并没有陈列于博物馆中,而是依旧鲜活的活跃在武侯人的视野之中,将积蕴的武侯文化通过面塑的载体留存于孩子们的心中,一双双手塑造一个个尚看不清形状的面团,看不见的武侯文化也在通过这一个个面团,塑造孩子们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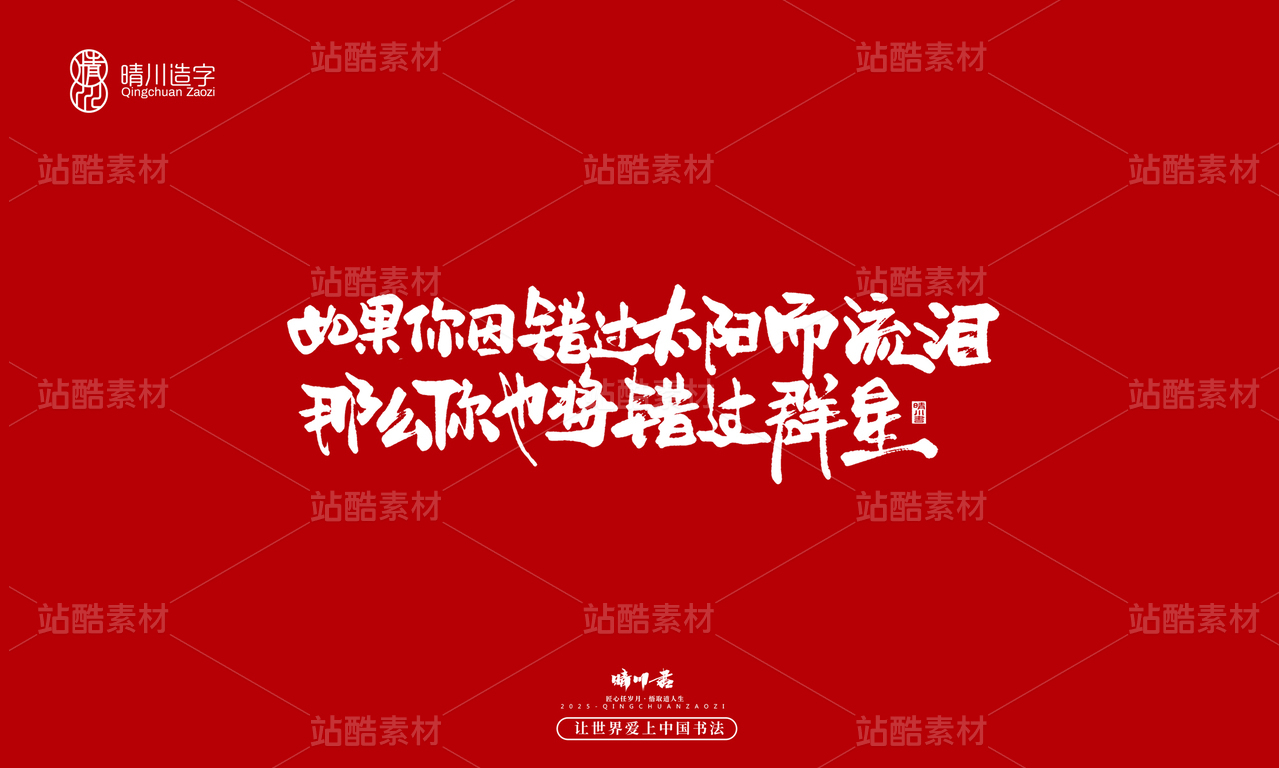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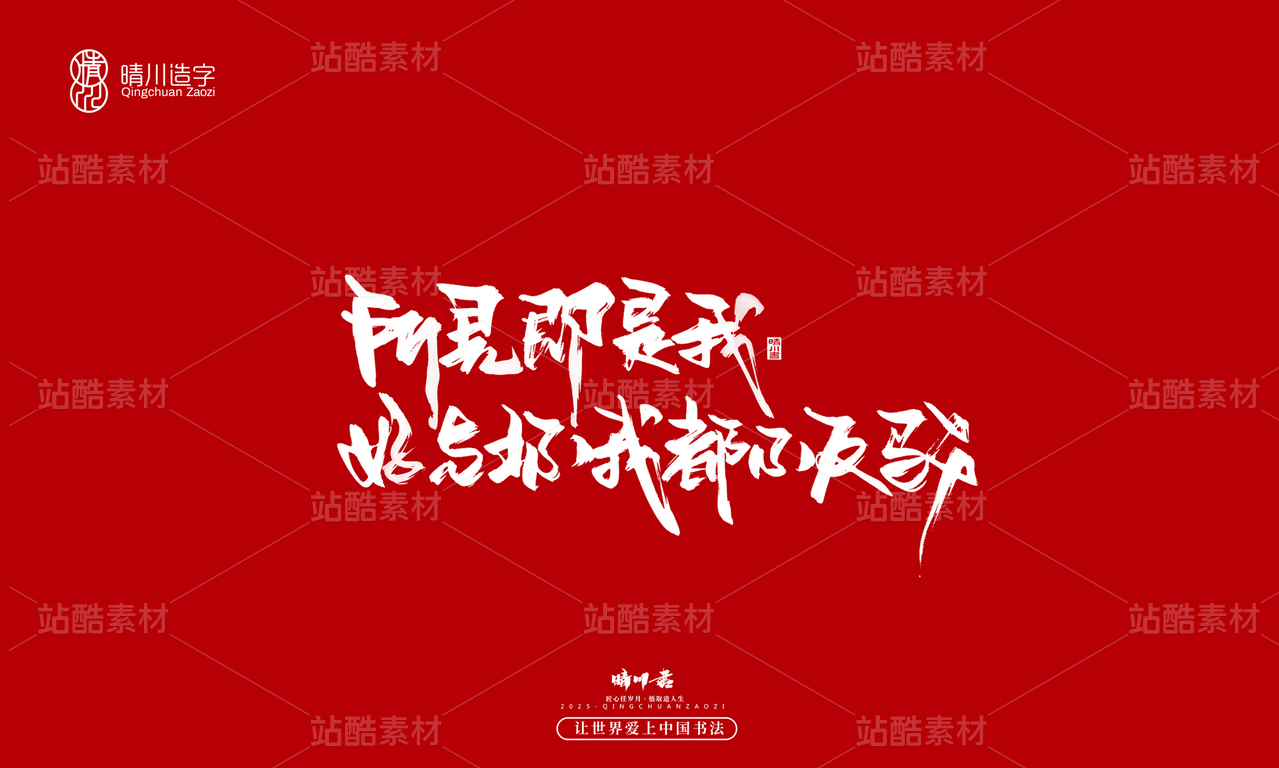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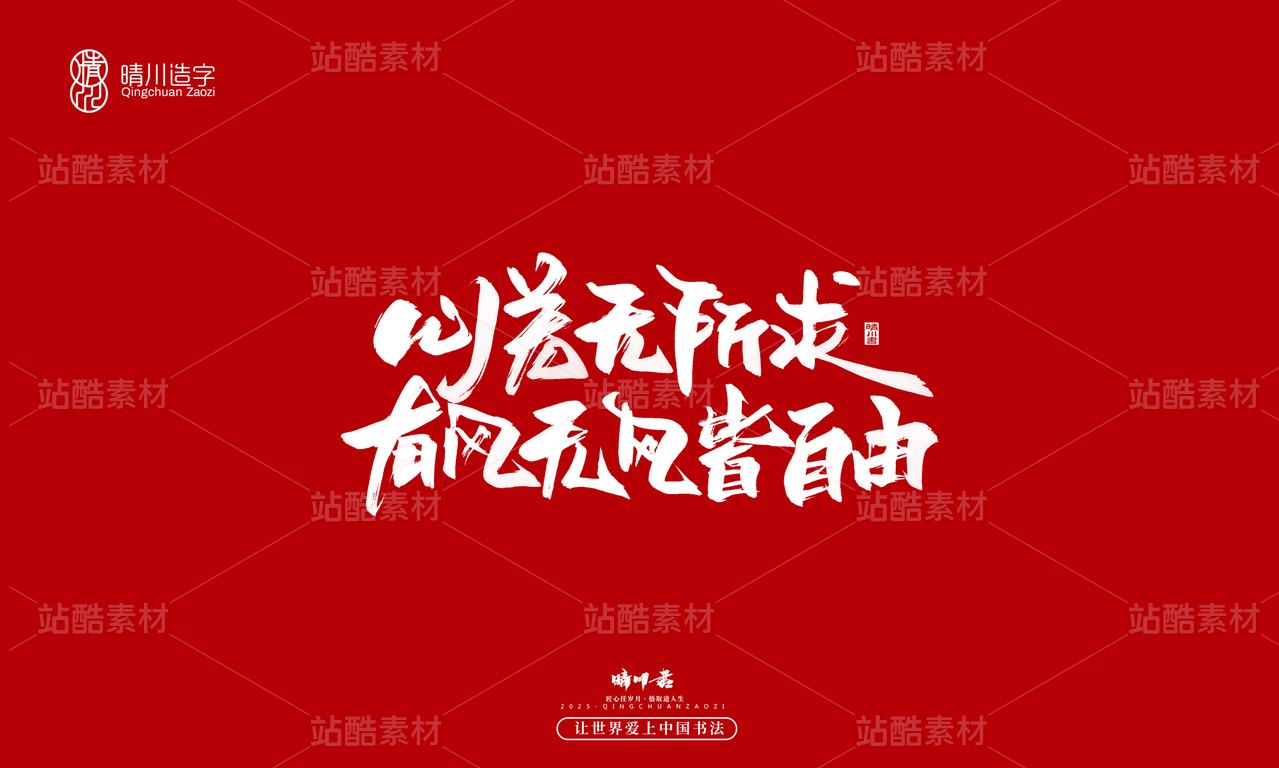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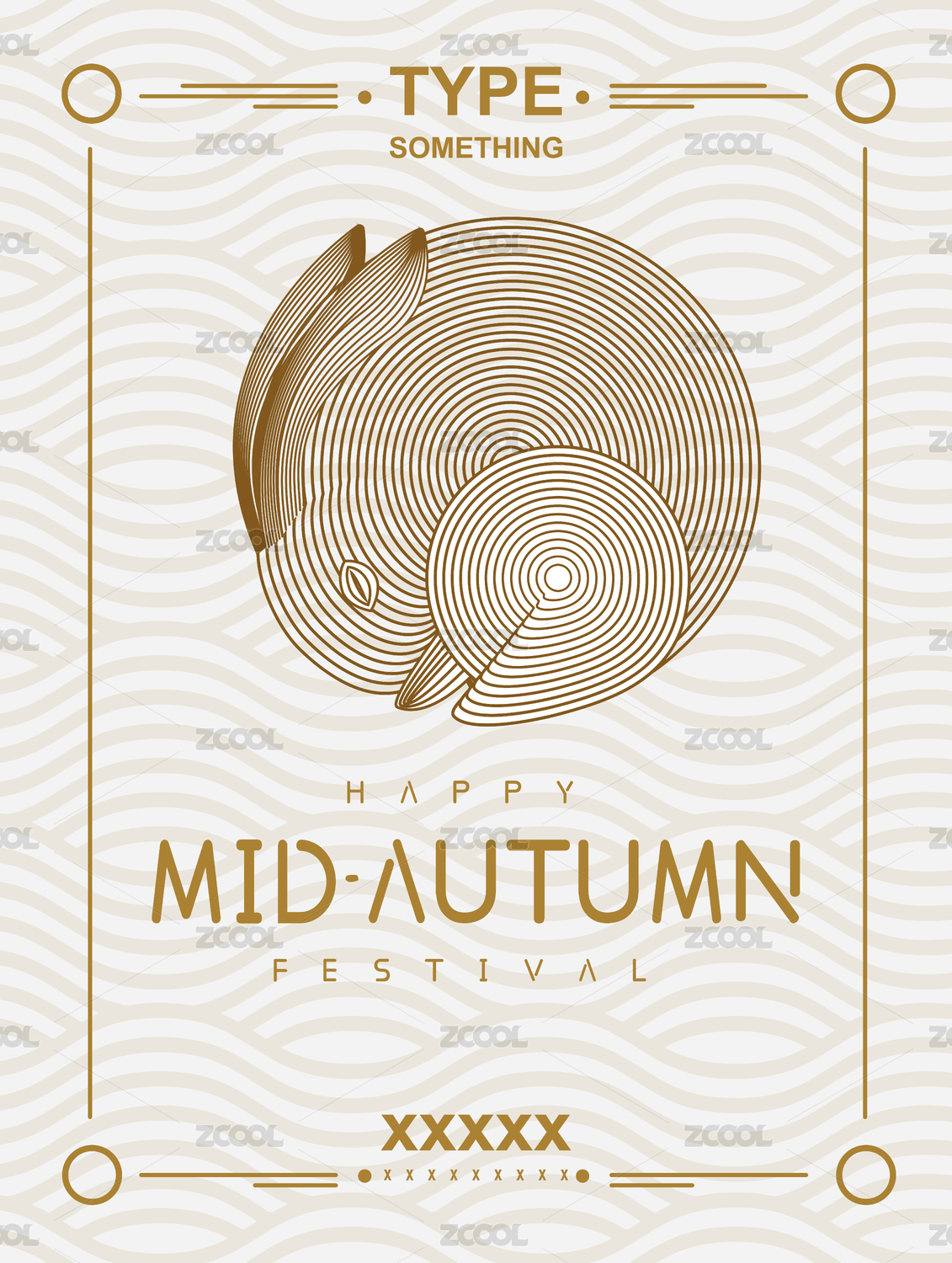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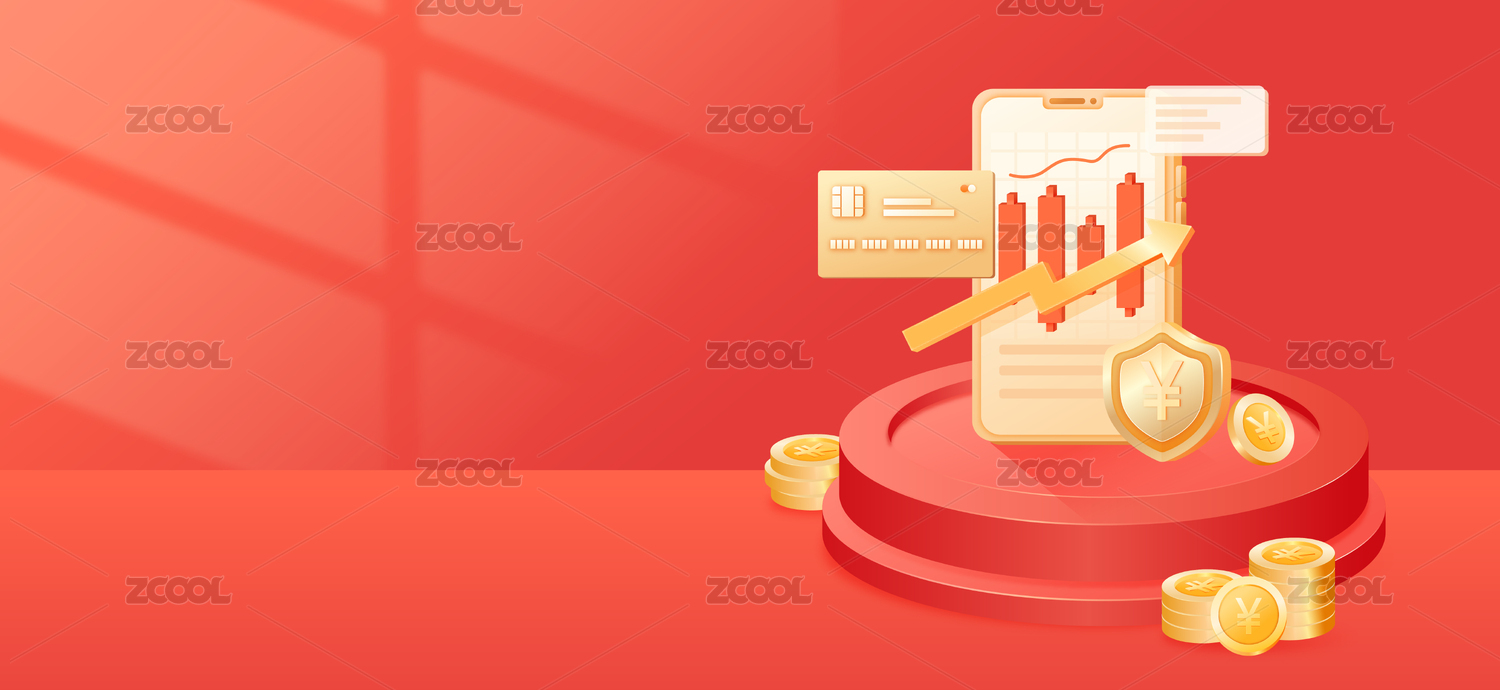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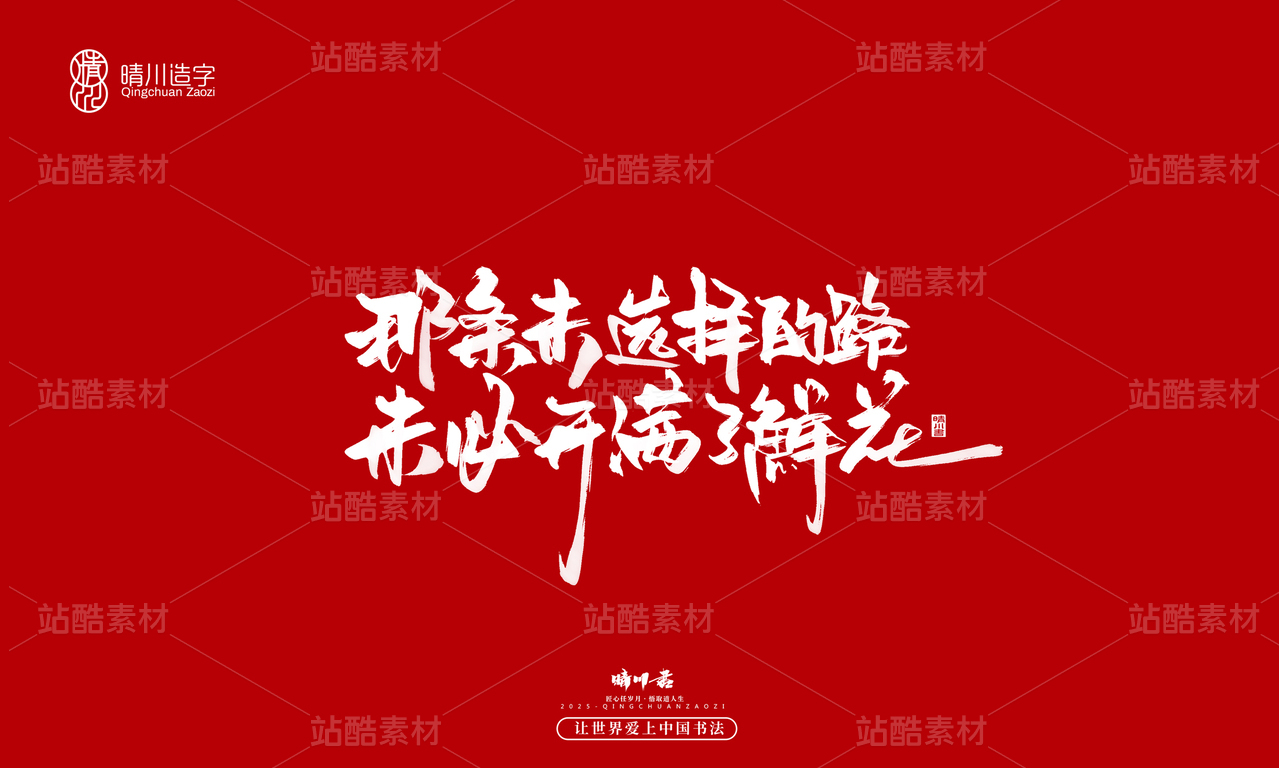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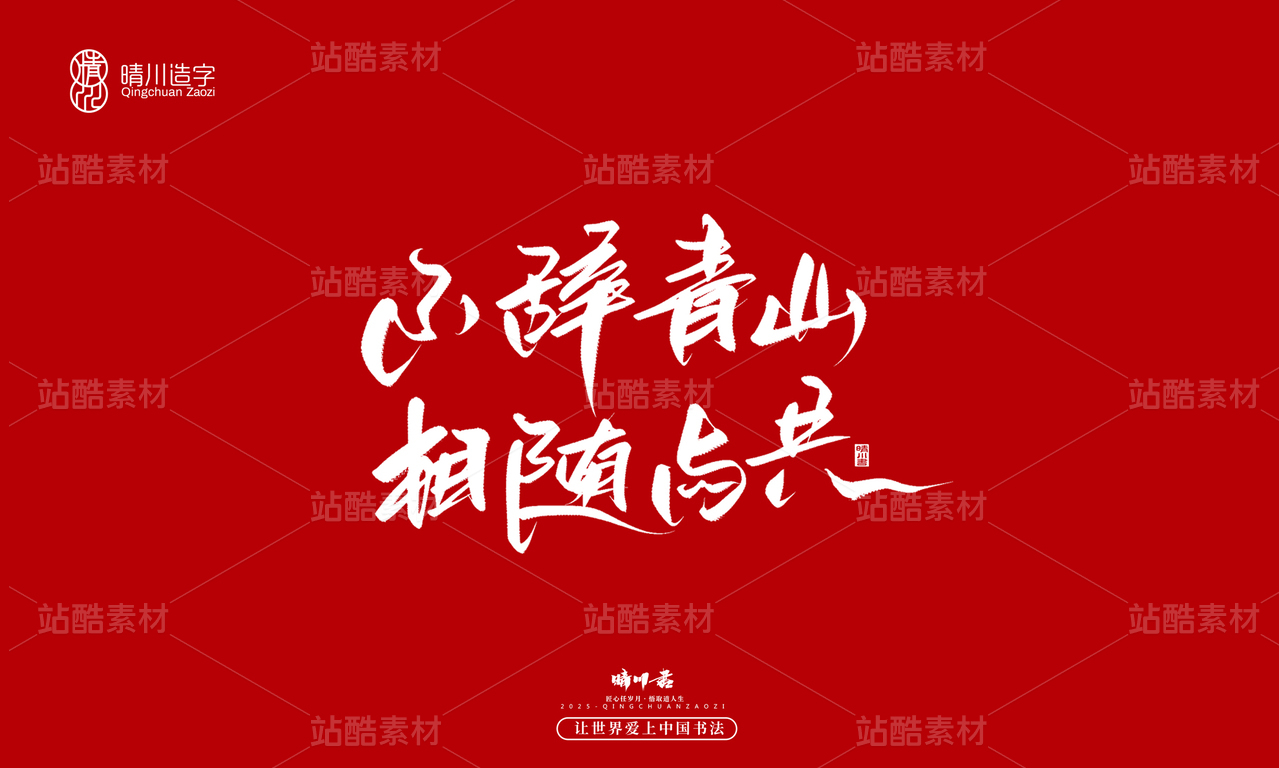









![ZAOV|各[苹]本事](https://img.zcool.cn/community/68d247ffa534901h5u6ly0544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w_520,h_390,limit_1/auto-orient,1/sharpen,100/quality,q_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