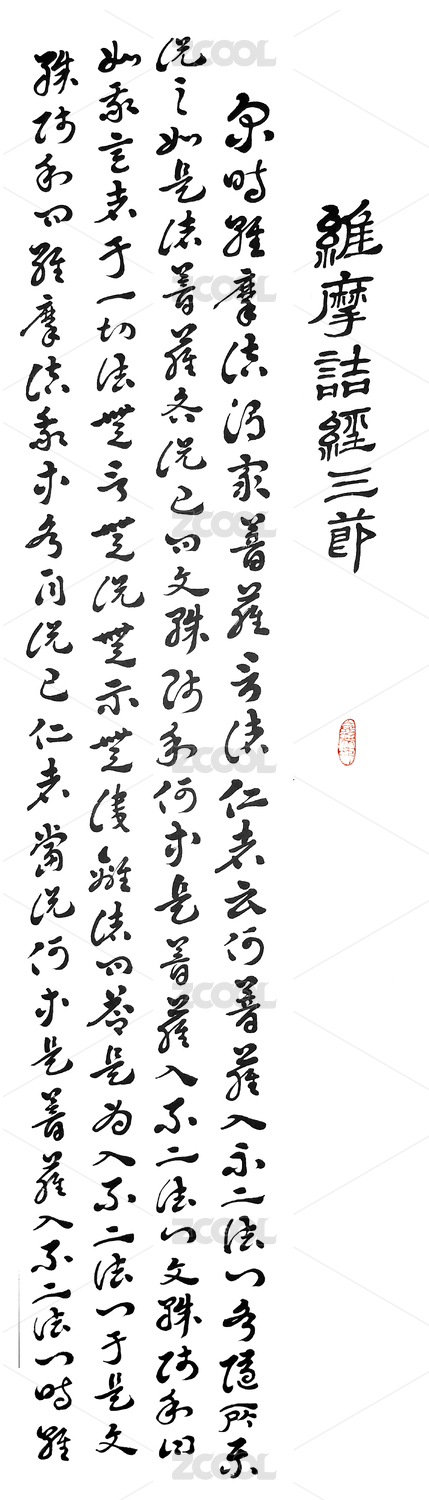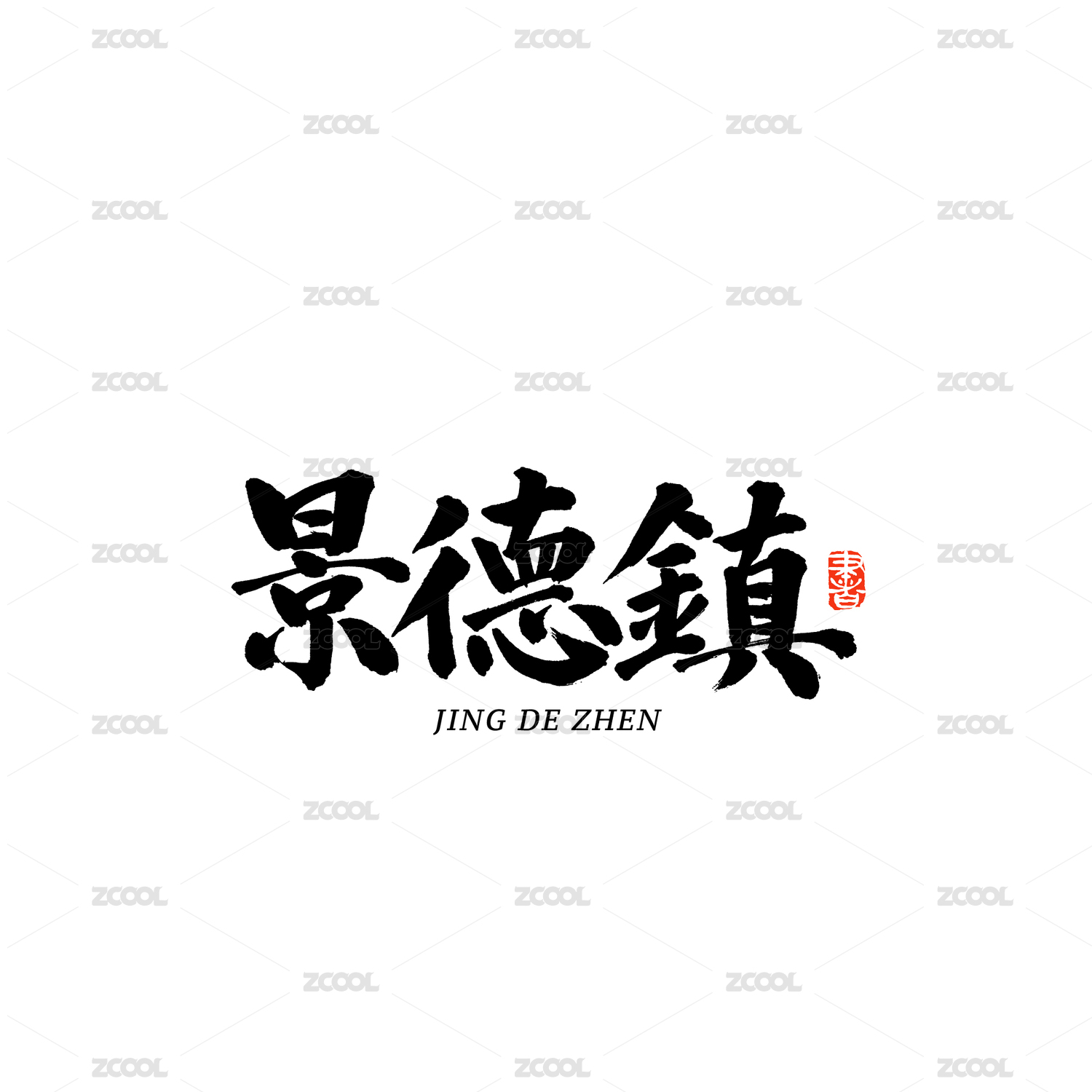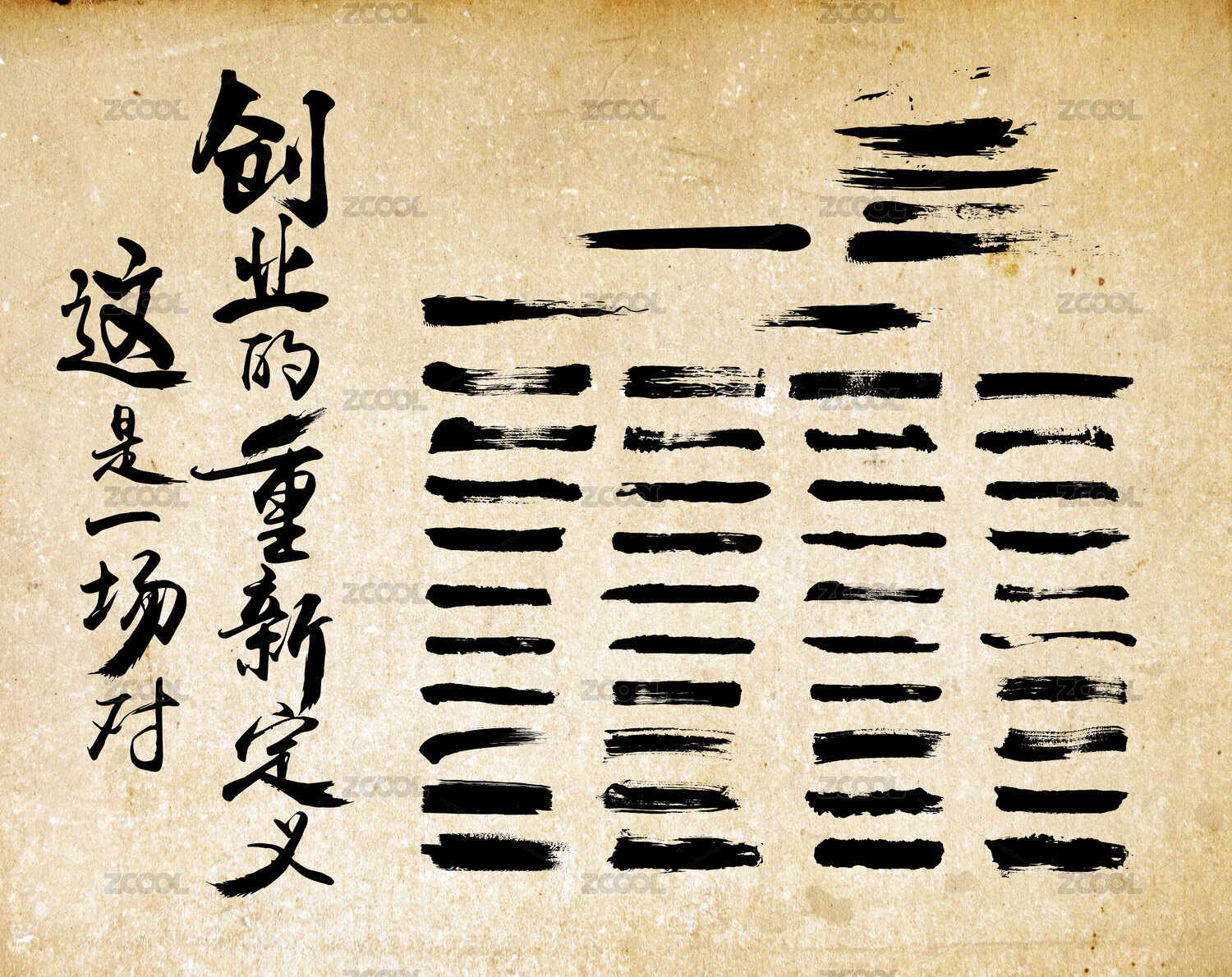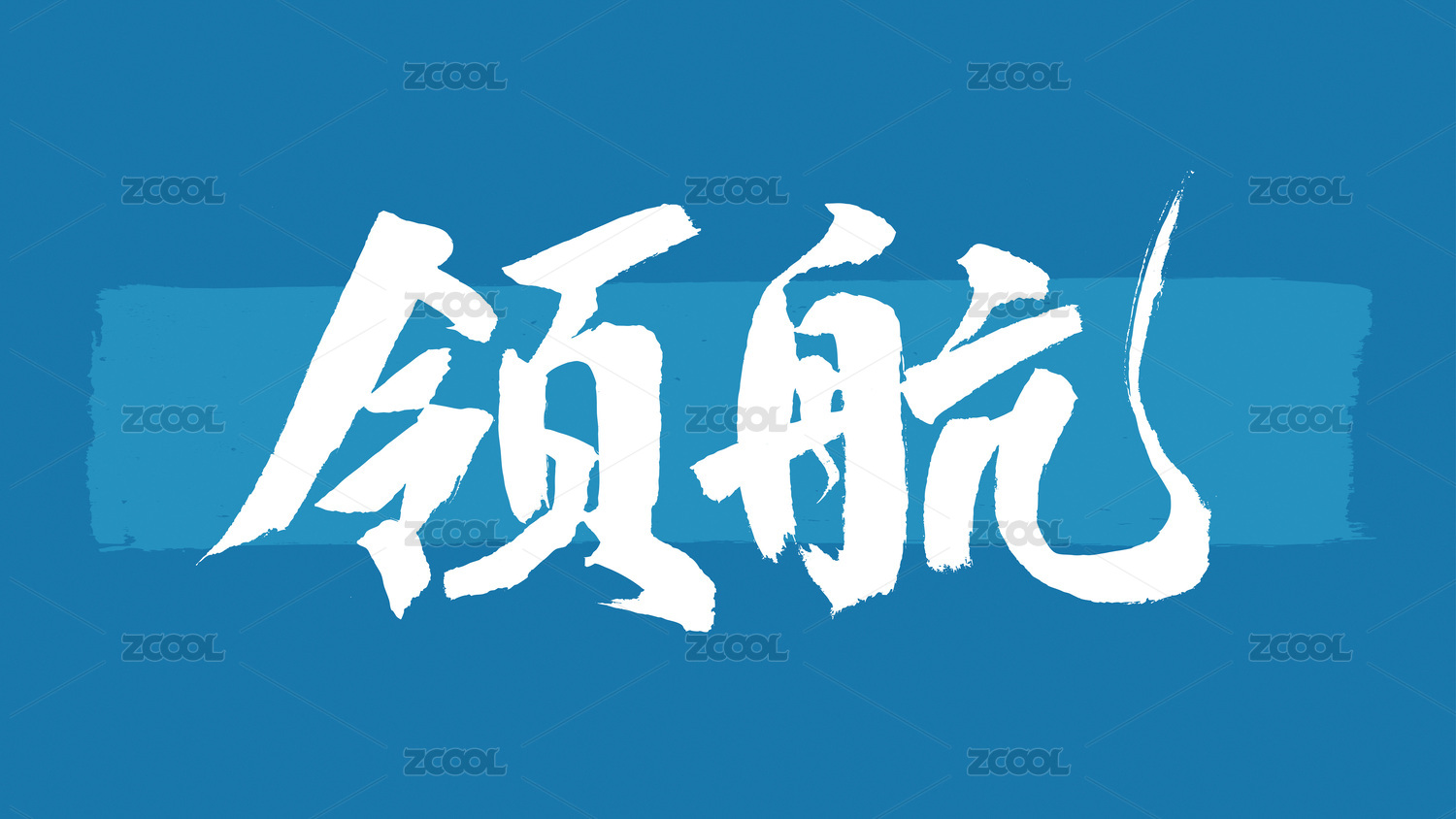刘浪《诗句的分行》
贵阳/概念设计师/9年前/205浏览
版权
刘浪《诗句的分行》
刘浪对于诗句的理解和分析,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看看哦,诗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代表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一下是我对诗句的感觉和理解:
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最直观的特征是分行。当一段文字以分行形式出现,就会本能地调动起读者诗的敏感,进入诗的语境。但如果读完发现,这些文字并无诗意,甚至横排起来还不如散文,分行就会成为一种原罪,一种被人嘲讽的对象。比如,诗是分行游戏,会敲回车的都是诗人,等等。这涉及一个基本的逻辑常识:诗是分行的,但分行的一定是诗吗?显然不是。在古代,诗是格律的,但符合格律的也不一定是诗。多少庸人,只要掌握格律那一套,往里填字,就能混成个诗人,和现在用分行冒充诗人如出一辙。他们都把形式作为掩体,来遮盖内在诗意的不足。诗与非诗之辨,决非只看外表这样皮相。真正的诗,即便横着写,它也是诗。它先是诗,然后才分行,而不是先分行,然后才是诗。
有人问:既然横竖都是诗,为何一定要竖着?这是由诗的本质决定的。诗的本质要求诗只有竖起来才能达到诗意的最大化,即突出语言和增加美感。
诗是语言的炼金术。被写成诗的文字,和一般文字,在含金量上有不啻天渊的差别。倘把它们揉在一起,不加以区分,无疑是对诗的蒙蔽。分行,就是为了去蔽,与日常语言划清界限,像一座尖峰,从语言的连绵起伏中孤耸出来。这并不陌生,我们写其他文体时,早已惯用这样的手法:为强调某个词或某句话,而令其单独成段,造成放大、突兀的效果。可见,分行是一种奢侈,是对重要文字的高级礼遇。诗,就要写得每一行都配得上这样的礼遇。很多人之所以写出非诗甚至反诗的东西,就是因为忘了分行的初衷,以为写诗就要分行,无论写的什么,先分行再说。分行在他们那里,成了最廉价的劳动,随便一段废话,敲几个回车就算是诗,这是对诗莫大的侮辱。
诗的美感既来自语言内部,有缤纷的意象,幽深的境界;也来自语言外部,有匀称的结构,动人的旋律。分行是为了增加语言外部的美:视觉美和听觉美(或曰建筑美和音韵美)。在这点上,古诗可谓做到了极致:以四字、五字或七字为一行,行中有调,行尾有韵。我们承认,若能淋漓地表现诗意,同时兼顾形式,那是最理想的。因为格律确实有一种能力:使情绪得到最有力的传达,且朗朗上口,易于传诵。但是,当古诗碰到现代文明,当格律遭遇现代意象,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借用戴望舒鞋子与脚的比喻,硬把自己的脚往古人的鞋子里去伸,结果当然只有削足适履,以减损诗意来妥协形式。新月派曾倡导的半格律体,随着新诗的发展而被淘汰,便是教训。白话是一种松弛的语言,富于弹性,不像文言绷得很紧,若受格律限制,难免拘谨,机械,乃至空洞。文笔矫健如闻一多者,也只是把《死水》写出了一些微澜,其整饬的外形下,用字的牵强和凑韵的窘态,还是比较明显的。
为了更深地开掘诗意而不是耽溺于格律的玩味,诗的散文化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倾向。这既符合诗的演变历史:从相对自由(古体诗),到极度规整(近体诗),再到逐步松散(词,小令),最后彻底解放(白话诗);也符合新诗自身的特质:古诗善于唤起感受,新诗善于唤起沉思,而沉思的叙述往往是缓慢的,渐进的,无法格律化的。新诗疏于形式,是要最大程度地触碰生活深处的诗意,因此它适合看,不适合吟咏。但疏于形式,并非不要形式。诗的形式,仍然可以借助恰当的分行来实现。其自由在于:诗没有固定的形式,因而没有固定的分行规则,适用于这首诗的分行,未必适用于下一首,但每首诗都有一个契合它的分行,需要诗人去感受和发现。这个过程十分隐秘,它基于一个人长期的诗歌训练所养成的艺术直觉,非理论文字能够说清道明。在此举两个特例。一个是马拉美的《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是一首排列混乱的诗
5
Report
声明
收藏
Share
相关推荐
in to comment
Add emoji
喜欢TA的作品吗?喜欢就快来夸夸TA吧!
You may like
相关收藏夹
Log in
5Log in and synchronize recommended records
收藏Log in and add to My Favorites
评论Log in and comment your thoughts
分享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