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的北京,天终于放晴了。我们比原定时间早到了30分钟,古奇已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初见,他似乎有些含蓄,在问及是否需要看看打印好的采访提纲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用,直接来吧。”聊天比预计的时间提前结束。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每天16:30雷打不动地要做一件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事:亲自接女儿放学。
40岁之前的古奇,重心一直扑在工作上。几年前,父母相继突然离世,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生活的优先级排序被重新打散、组合。古奇说,当你直面过“死亡”,才会迎来真正的“成熟”,这也是死亡唯一令人欣慰的地方。他决定从零开始创立一个专注于殡葬领域的新品牌:归丛。这不仅是行业的美学升级,古奇更是从中找到了一条似乎能重新焕发自我和探索世界欲望的新路径——在中国做死亡教育。“当下多数人的生活、心理都是失衡的,而死亡教育是在帮助你校准感受力的过程。”虽然至今尚未盈利,这条未被探索过的路,还有很多的艰难险阻等在前方。但他想要长久做下去的态度和决心,却十分坚定。
2024年9月,是古奇创办的殡葬品牌“归丛”一周年的月份。这位42岁的创始人,曾在14年前创立过颠覆了中国家具领域审美的“梵几”,很多人也因此认识了他。2020年,他退出管理层。三年后,他仅花了五个月就推出了第一批殡葬产品,而第一个购买的用户就是著名导演陈可辛。骨灰盒至今仍被摆放在陈可辛父亲的家中。之后,慕名而来的还有知名媒体人、作家洪晃。
而这一切的开始,要追溯到2019年。古奇的父亲突然被查出癌症晚期,没过几个月便离世了。没想到,2021年噩耗再次袭来,母亲也离开了他。这对他的打击,比预想的强烈得多。
与参加葬礼不同的是,亲自为父母办葬礼让他切实地感受到,泱泱大国各行各业都在齐头并进,唯有殡葬业停滞不前。“选择性真的太小了。”他放弃了从“梵几”离开后做艺术性家具的初衷,转战到了殡葬业。“甚至会有人觉得,专挑这样一个小众赛道,是在赚死人的钱。”
勇闯殡葬领域,并不是靠着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对行业的敏感度和未来可能性的预判,是古奇这么多年从摸爬滚打中积累形成的。一方面,古奇是设计专业出身,毕业后开过咖啡馆,做过室内设计,后来又成了“梵几”家具的创始人,一干就是很多年。他觉得中国殡葬领域发展到现在,应该具有一个当代审美,这是他作为设计师的责任。
另一方面,更大的隐蔽性原因是,父母对自己深刻的爱再也无处回馈。这种切肤的感受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他把“归丛”的初衷描述成“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美学产品。其实,父母相继离世这件事,就像我死过一遍一样。我是在自救。”所以对现在的他来说,任何误解都没那么重要。“归丛”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应运而生了。
当年,家具品牌取名“梵几”,是取自净空之意。“归丛”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意为回归安然之境。其背后有着中国传统的轮回之感:灵魂再次重启,生生不息。
所有的产品中,一半以上都是由古奇亲手设计。一个完整的产品从草图到落地,大约需要至少两三个月。
与选材、找工厂相比,在保证美感和品质的高要求下,如何将传统殡葬的工艺产品——如纸扎——完好地运输到使用者手里,对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使用感和成本之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真的很难。”
目前,“归丛”一共有二三十款产品,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骨灰盒是最核心的,以罐、盒为主;然后是葬礼中涉及的氛围道具,如香烛、纸扎、花束和袖章……最后是日常缅怀仪式用品,如灵龛、灵牌等等。
在所有的产品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款名为“挽月”的白色珠圆陶瓷灵罐。挽月,亦是以月缅怀,寄哀思与明月,让归途的路安然宁静之意。还有一款灵盒“无隅”,由古奇亲手设计,以纯净的白玉为核心,两侧由温和的橡木围合。灵感来自父亲临别之际,用厚重温暖的大手握捧他双手的触感。这份爱与力量在他的心中从未被时间削弱过。
“(产品)是否受欢迎,也是个蛮玄妙的事。”有人因为价格适中,有人被寓意触动。“其实‘无隅’的价格并不低,一万多,但销量颇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和父母对自己这一生付出的精力、情感相比,分量远不止于此。”
整个团队会定期收集各个平台的用户评论。“给我父亲买了这个殡葬罐之后,他成了火葬场最靓的仔。”这条诙谐的留言,让古奇觉得还蛮酷的。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女儿的留言:我希望可以在灵牌上刻上“隔着世界,永远爱你
♾️
”。作为父亲,古奇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背后,死亡带给她的不是悲伤、难过,而是作为父母的一种平静的力量。
这位女儿近期又联系了他们,希望购买一款其他的殡葬产品,这是令古奇没想到的。“我曾以为,这是一锤子的买卖。”这种“刻板印象”也在他最近一次拜访朋友的宠物殡葬店经历中,被打破了。朋友分享到,经常有人时不时地就来这里,刻一个有着宠物肖像的小吊坠放在家里。古奇这才领悟到,无法被安放、割舍的情感,才是让消费产生长尾效应的最根本动力。
在对待每一个用户层面,“归丛”无疑是真挚的。按照商业规则,如此高成本的产品,不应该存在退换服务。但古奇深知,自己面对的是心里有“洞”的人,只要不是无理要求或恶意竞争,仅仅是不喜欢玉石的纹理之类的要求,团队都会尽可能满足。“虽然公司尚未盈利,但这些情感的互动和付出我完全可以承受。”
在中国,遗体告别是非常近代才出现的。现在,这件事和火化基本在殡仪馆完成。“冰冷、模块化、草率”是大众对它的初印象。古奇觉得,死亡是中国人最“避讳”的话题。殡葬业进入流程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但回归到人性角度,其实是一种弃权的表现。
流程越来越简化,但生者的情绪还没有找到出口。古奇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和愿景,就是提供定制化的告别仪式。“更准确的描述是「唤醒」。”在他看来,告别不需要在殡仪馆内完成,也不该是仓促的,甚至是不需要真实的遗体。它是一场和去世之人关系亲密的、小型的“精神重聚”。
古奇母亲去世时,当时的情况让他没办法回东北,因此,母亲的葬礼仍未正式地举办过。这对古奇、对母亲的朋友来说,至今都是一个心结。“可能时机还没到吧。”
古奇这样描述一场理想的告别仪式:“假设我们可以在空间的中央摆放一张逝者的照片,围绕着的是他/她成长的各个阶段的影像。所有来这里参加告别的人,可以分别讲述一段自己和逝者之间的故事,那么这些回忆就能共同构建出一个立体、丰富的给予过彼此爱的人的一生。”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而告别仪式不仅是对生者的心灵慰藉,更是逝者来过这个世界的重要印记。
这个设想,早已在古奇的脑海中和草稿纸上反复涂抹过很多次,落地指日可待。
古奇的父亲在20年前便和古奇谈及过自己的安葬方式:将骨灰撒在山上。能按照父亲的意愿完成他想做的事,古奇非常安心。他对自己的殡葬方式早已了然于心: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延续父亲的方式死在山上,然后遗体自然分解,把一切都回归宇宙。”因为最近痴迷研究中国各地的葬法,他才知道这种方式和藏族的“树葬”不谋而合,区别在于树葬最终会有人把“遗体”收回去。
相较于传统的土葬,国内现在更推崇的是海葬,目前已经在上海得到了实践和推行。2024年6月23日,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在全国首次将患者“临终决定权”——生前预嘱——写入地方性法规,并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举在当时引发了各界的激烈讨论。
“将临终尊严握在自己的手里,是非常人性化的。而提前交代,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
近几年,大众都在消费降级,很多人开始在线上挑选产品,对自我价值、生活、人生要如何度过的观念产生了巨大转变。已逐渐成为中流砥柱的90后,对产品的接受度最高,甚至想要更潮牌、更绚烂的设计。在古奇看来,这些征兆都暗含着,事情在朝着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
谈及是否存在负面评价,古奇的脸上有一丝挣扎,但很快便消失了。他提起某次和一位抖音大V聊天,对方的一段话深深地刺痛了他。“附近找殡葬店随便买一下就完事了,你是不是高估中国人了?”转念,古奇想到自己做这件事的初衷,也并不是想要满足所有人。他更深知,人的观念是最难改变的。
现在,很多人无论上班还是生活,都会产生一种“既疲累又无望”的感觉。一方面是焦虑感,另一方面是被很多旁枝末节混淆了。“我现在完全可以接受,身边很多优秀的设计师朋友正处于巅峰状态。即便曾经站在聚光灯下,如今也会被更迭掉。我不会再做无谓的比较,他在书写他的人生,而我有我想追求的版本。”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的作者欧文·亚隆,在书中列举了参议员理查德·纽伯格在得知自己患癌症之后,再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参议员席位、银行存款或自由世界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他和朋友共进午餐,搔墨菲的耳朵、妻子的陪伴 ,在冰箱里寻找橙汁、咖啡或蛋糕。「每每想起自己在过去,即使在健康状况最佳的时候,因为妄自尊大、虚伪的价值和空想出来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糟蹋自己生命的事情,我都会不寒而栗。」
这一观点和古奇理解的「死亡教育」不谋而合:站在人生的终点回看,能够帮助每个人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并诚实地面对生活。
现在,孩子和太太被古奇排在了人生首位。每天,他早上8点送完女儿上学便到办公室工作,下午4点30分会接女儿放学,晚上也会陪伴孩子休息。在团队里,他扮演着一个“脑力”输出的角色,执行和落地的部分便交给团队的其他同事完成。
“有些事,我只能使它发生,至于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是不能奢求的。就像一个石头投进水中,能激起一点点涟漪就很好了。”带着这样的念头,古奇想要一直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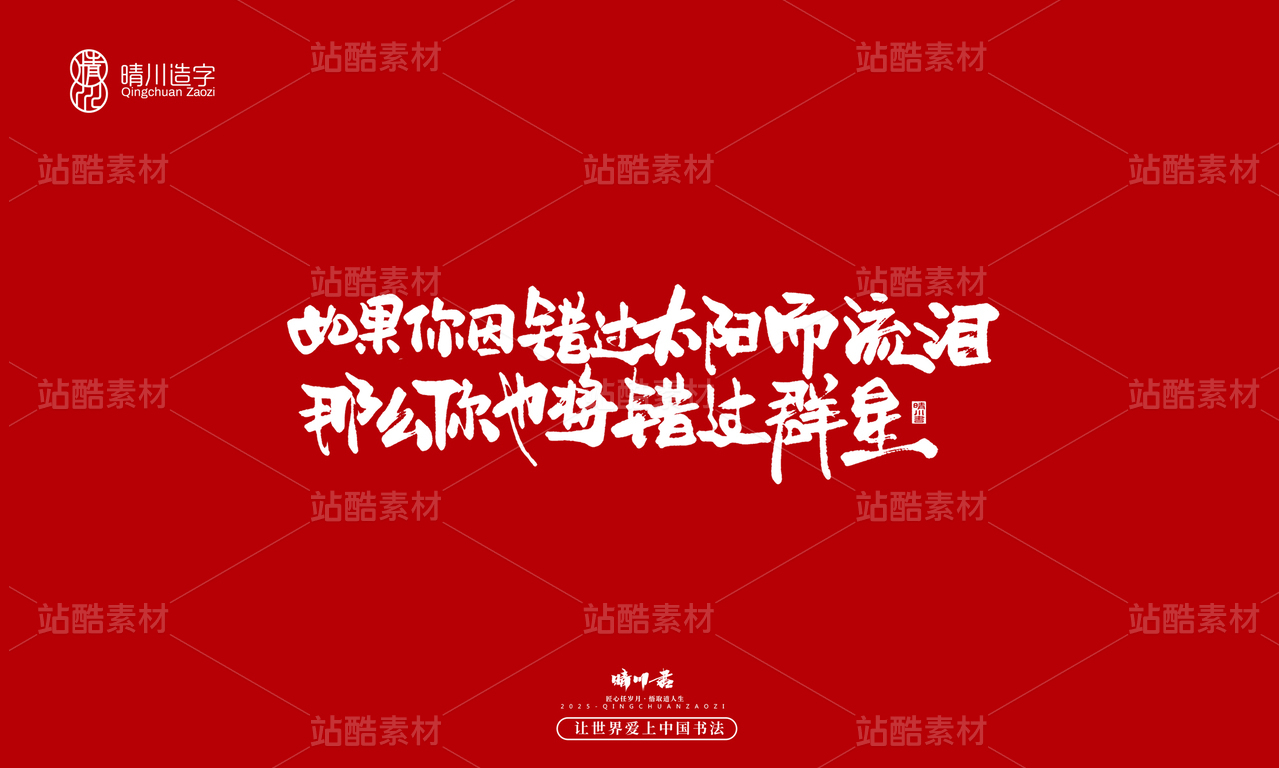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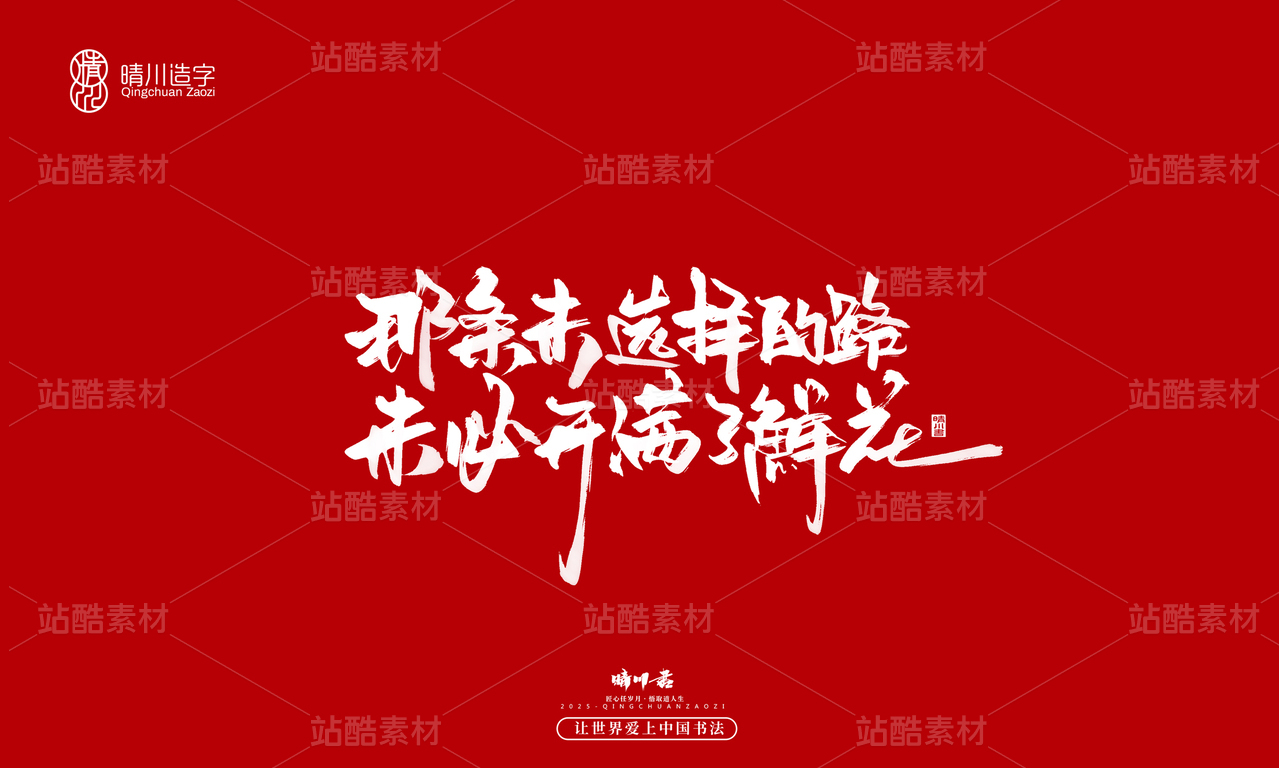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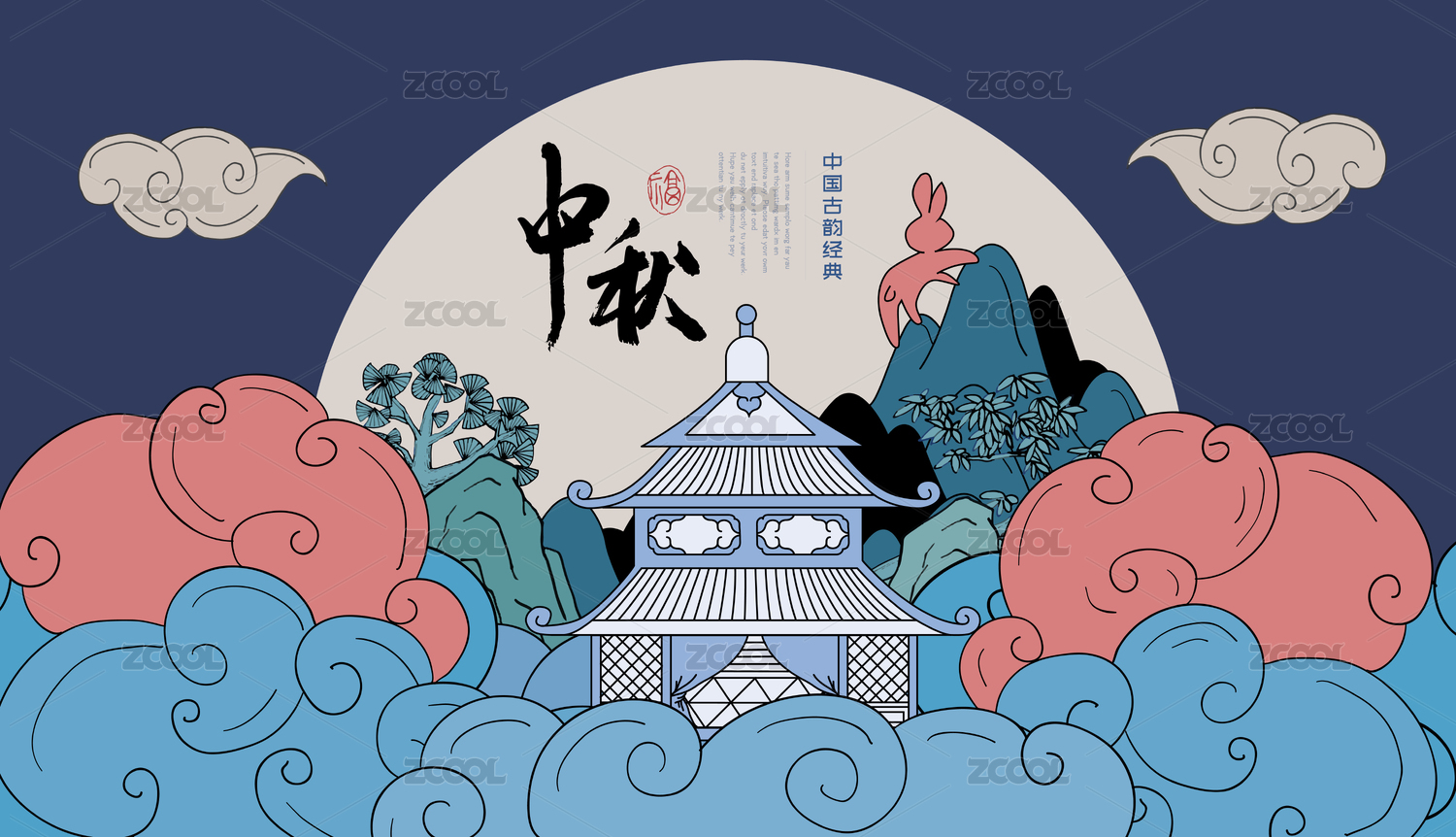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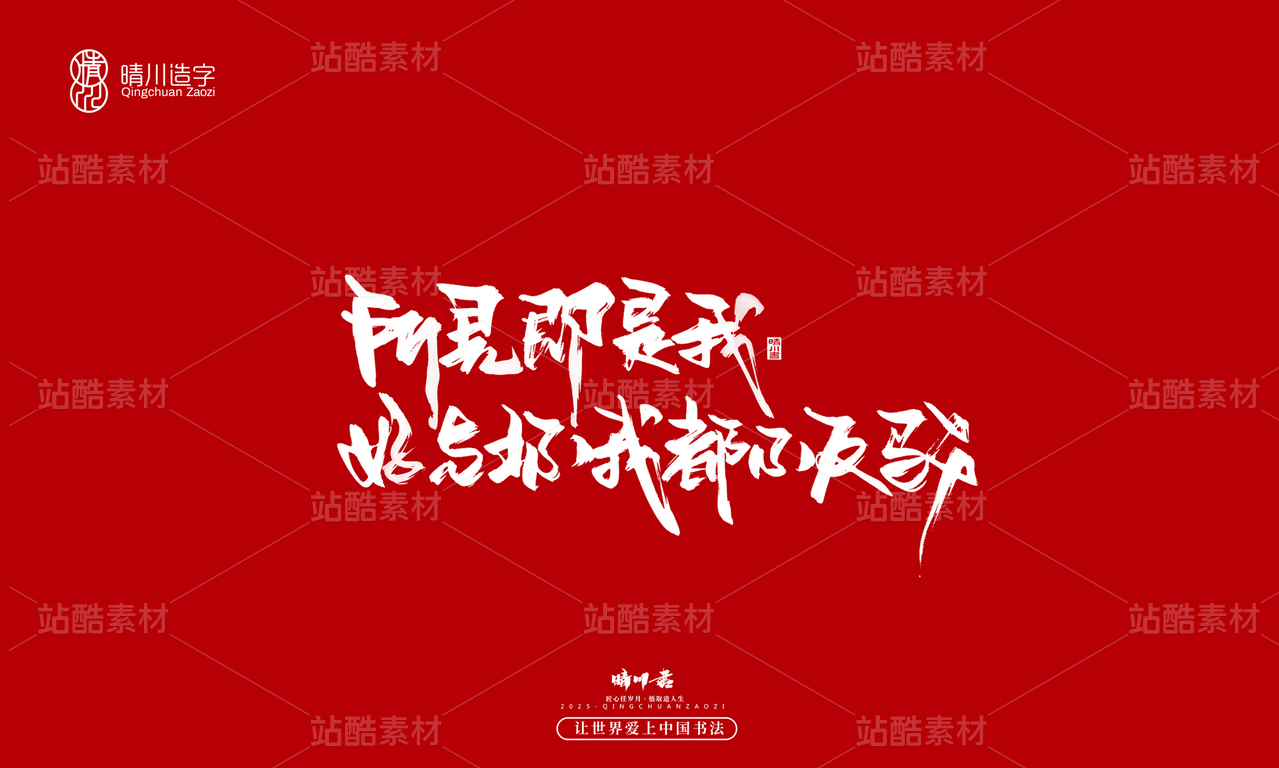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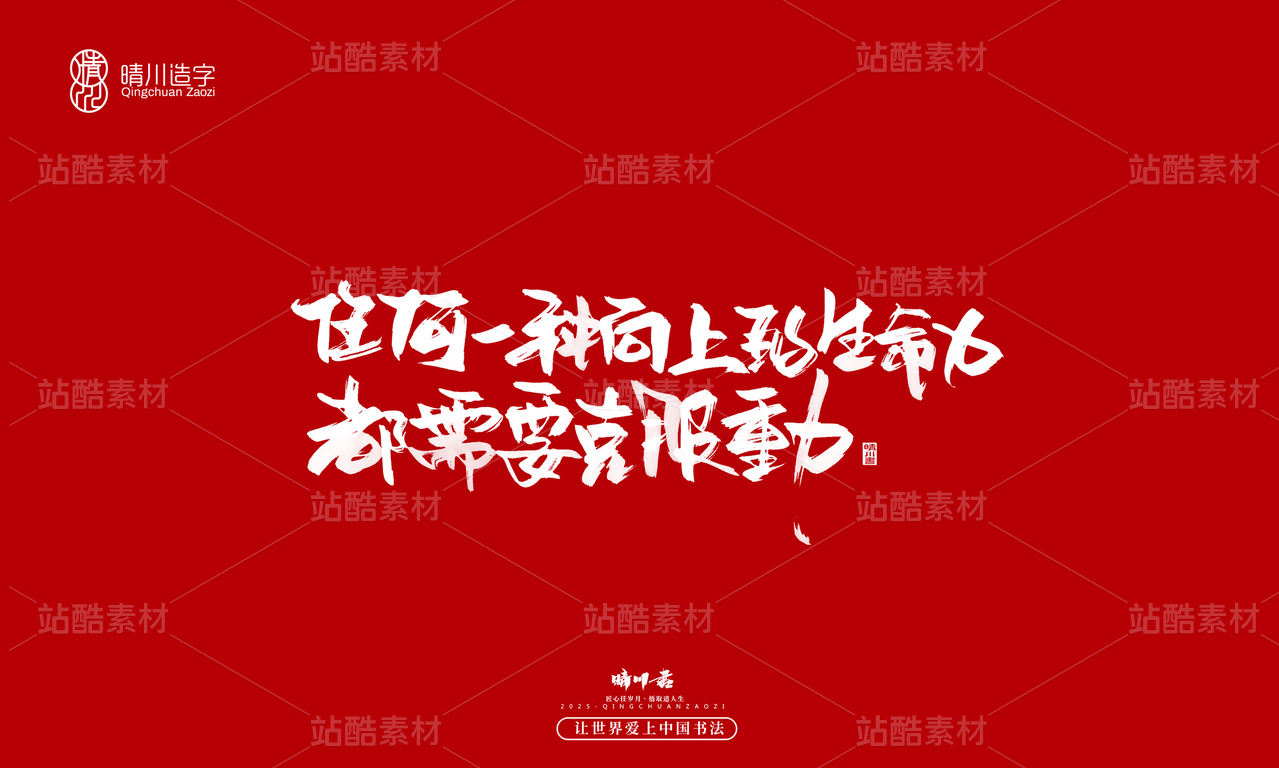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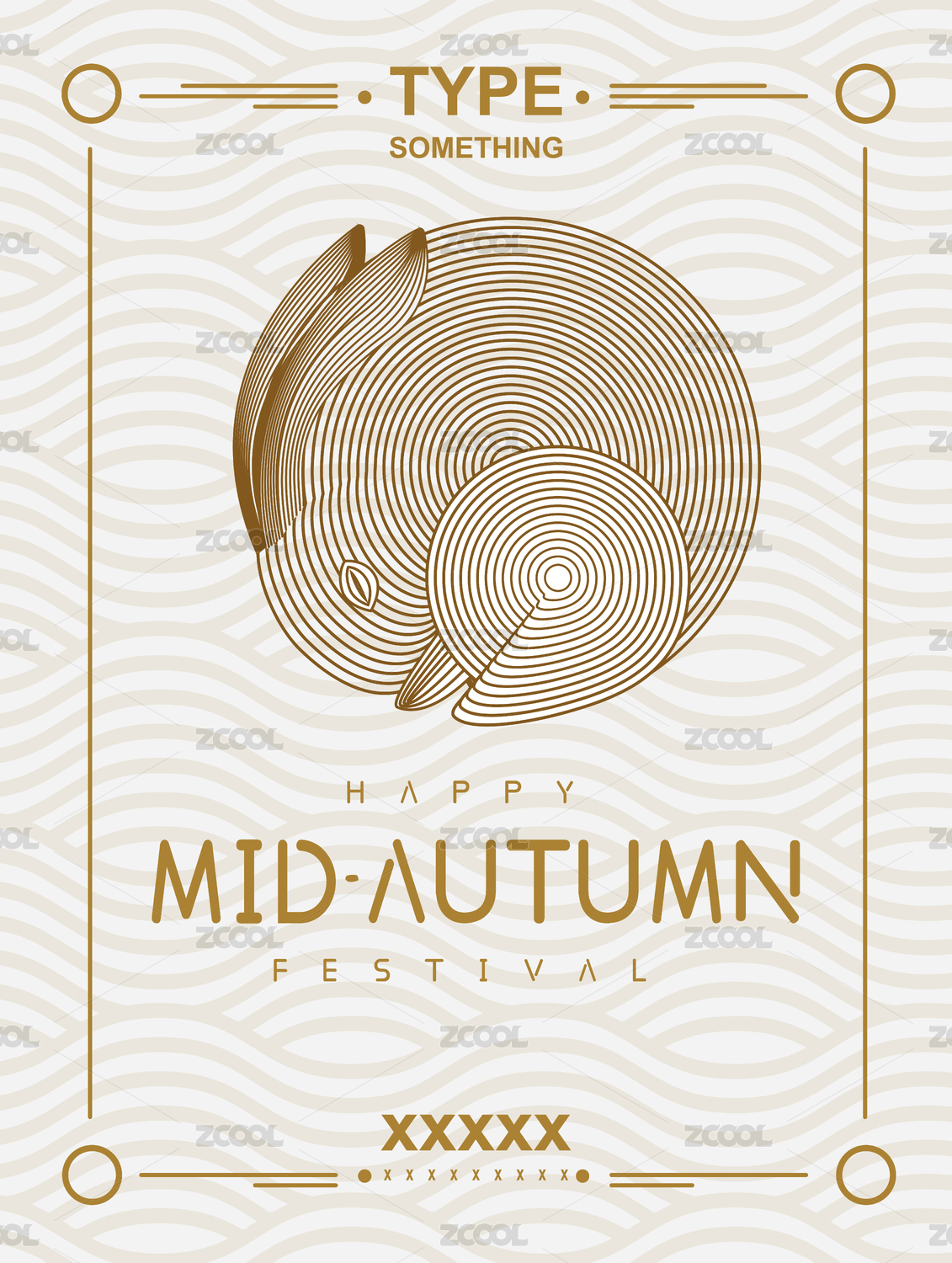






![ZAOV|各[苹]本事](https://img.zcool.cn/community/68d247ffa534901h5u6ly0544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w_520,h_390,limit_1/auto-orient,1/sharpen,100/quality,q_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