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写序的陈昉先生坦率地说,若你出这个书,序言就用这句吧:“如果受過傷真能擁有一雙翅膀 那地球一定是座空蕩蕩的城邦”
所以我便很不假思索地把这句话,作为我《花开的暗暝》诗歌集扉页上的“题记”。洋洋洒洒写了十年诗歌,若去捡从前所有的诗稿,怎么也能码成如‘切糕’大小的纸堆了,如今呈于一书,又将选出一句作为“题记”,本是纠结的问题,如今由陈昉先生作序+提议,这本书便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好吧,简单地说,我的诗歌集,黑夜之书《花开的暗暝》。请不要问我的诗是什么风格,我写的其实是歌词,但是,我的歌词,往往都是诗,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本书,收录了我自进大学以前,由’白痴‘般地开始写诗歌,谈了无数场爱情,大学毕业,初踏旅程,犹遇大海,婚礼写的歌,在厦门写的歌,在青岛写的歌,在西贡写的歌,在台湾写的歌,一直直到近年所有最好的作品,收录了一下,成册独立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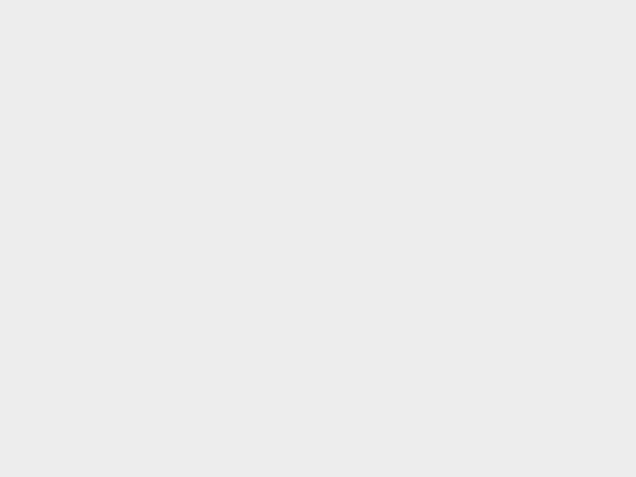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诗歌集的外封套不必很繁琐,一个“花”自就能囊获我想告诉大家的东西。创意来自诗歌集第一章的题言:“今夜,幸福不是在黑暗中綻放,而是在月光下盛開⋯⋯”
我的诗歌,其实只是,夜晚的黑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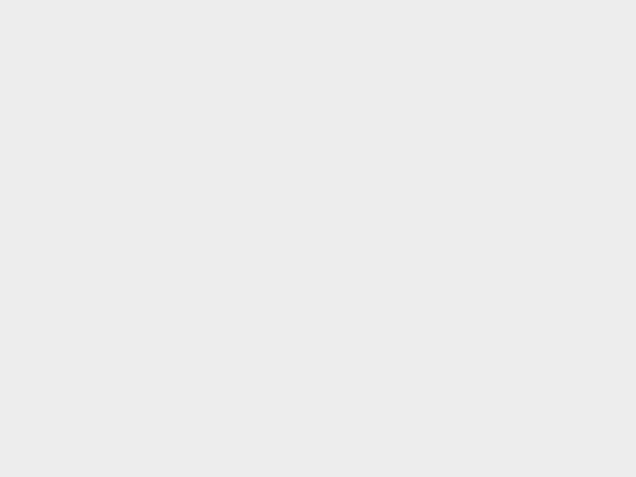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外封皮采用迷迭金硫酸纸,配墨黑大字。其实选纸的时候,我不觉得除了雅金之外,还有什么能衬托一个黑色的“花”字。就好像我书里有一句话:“⋯⋯好像在告訴人們,只要在一起,他們就能阻擋住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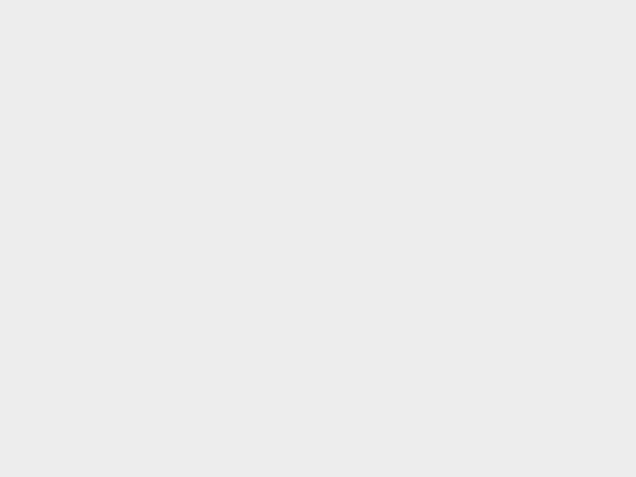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原本想如同全书的设计一样,用一个很精致的小字来装饰封皮,后来大胆推翻了:把字撑满,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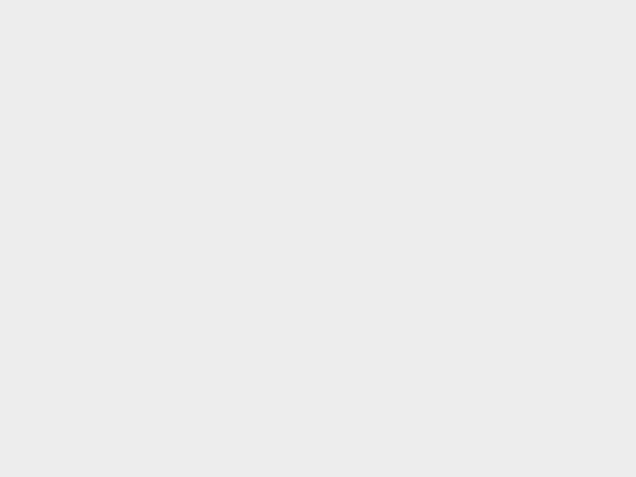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剥开封皮,诗歌集封面选用全黑。虽然很多设计同行总是爱说,你也懂的,黑面,终归不容易出错,是安全方案。不过我从来不这么想,黑也有它的无数种黑,通过设计+印刷+感官几重轮番折腾考验,出来的黯羽之色是否还是我们预念的那般,这着实太难了。我爱黑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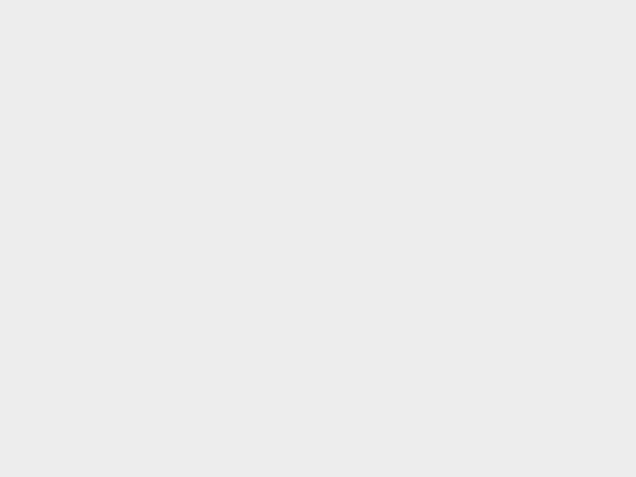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全书钢筋精致的小字体设计很多,只有长期熟悉我作品的老兄弟们,有时能从细漏里,眸见一些久违的东西。譬如我最早开始做独立设计师的时候,’公司‘的名字后缀是“艺术共和国”之类的不成熟用语。但是老实话,年轻真的够劲,留年轻一条活路多好,成熟是好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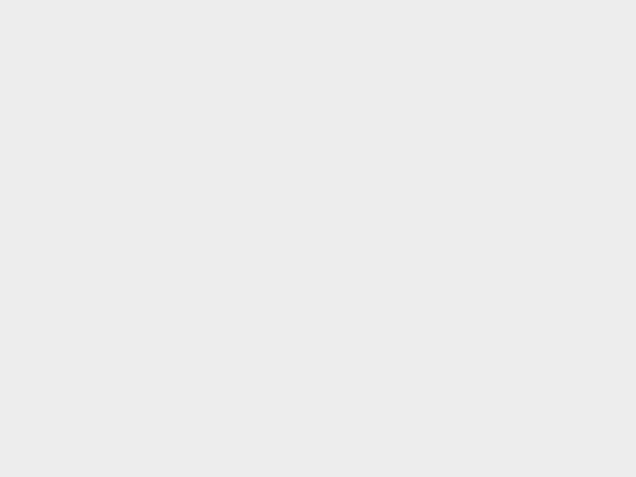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这个头像我暗藏了很多年,如今预备出书了,最终还是回过头去,从早已破败了’老厝‘里翻出这张照片,用曾经没有的调色功力,重新修复色彩,作为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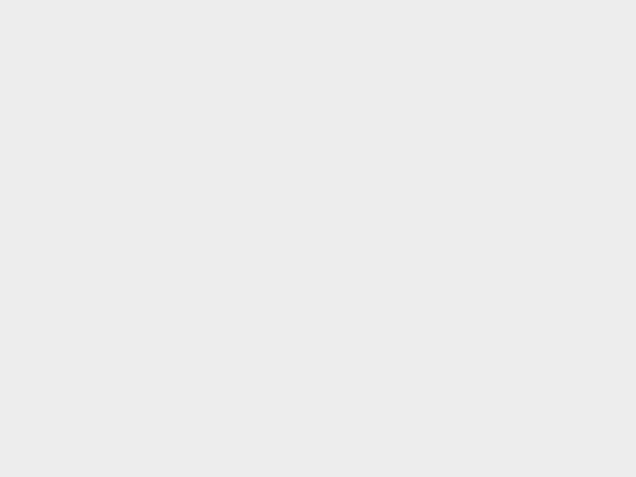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封面的标题栏,我不再使用最时髦,最in,最’微‘化的风格。而是另辟蹊径,回想从前老掉牙的美国杂志中的一些经典,呈如此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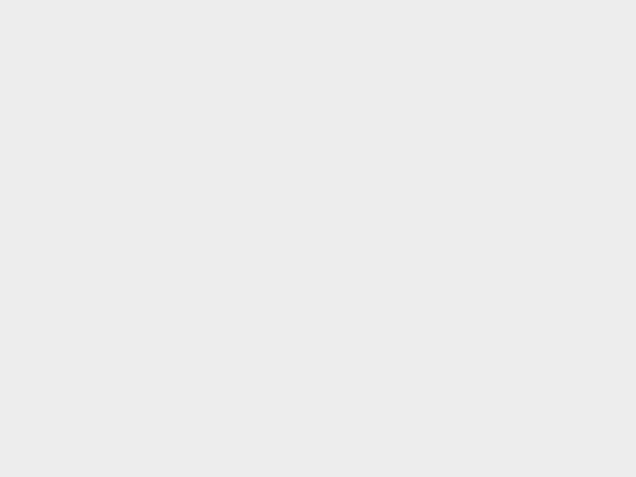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近期才明白二维码和一些最新的APP知识,觉得不学新东西确实不行,因为这些新东西的发明者,确实是有主意的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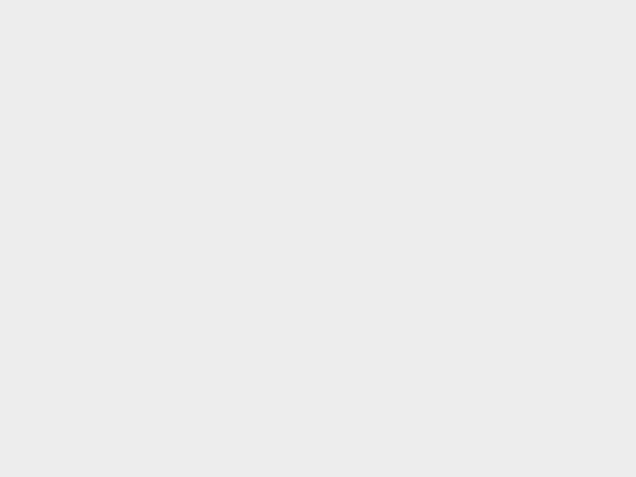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目录设计。其实,诗歌集并不一定需要目录,目录有什么用?目录拘泥的随性的风。但是目录还是应该留作不时之需,所以,目录设计得也较像随性的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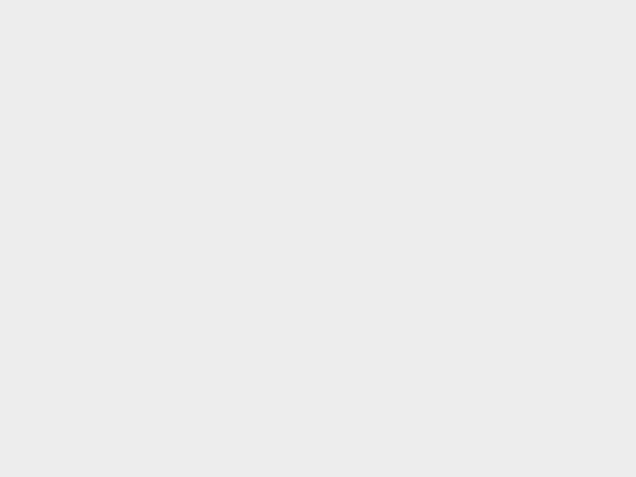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题记:“如果受過傷真能擁有一雙翅膀,那地球一定是座空蕩蕩的城邦”。
书中很多文字采用删除线妆点。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些文字都是很古早的记忆了。我们是不是,总是在丢弃曾经温热的老记忆,老朋友?这些无可避免,只是相信,被现实所迫而删除的,未必就一定把他扔掉。相识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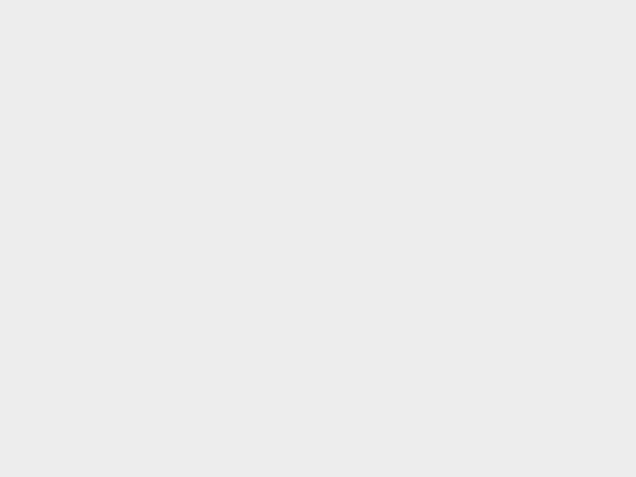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我没有使用任何一张,近年来自己成熟的独立摄影作品,作为书中的插图。
因为它们任何一张,都是后来创作的东西,不能表现我10年写作路途上的点滴真实记录。
所以,我使用了很多曾经曾经再曾经,许多必须我花上巨大的力气,修复老硬盘,才找回来的老照片。用一种类似在老相机里藏太久,严重漏光的风格,来呈现我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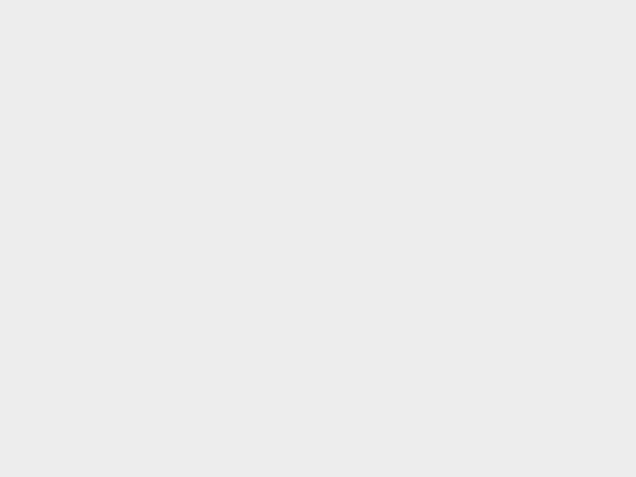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诗歌集中很多章节的名字,都比较美。譬如《岛岸迟笔》,《黯羽蔷薇》,《佛死之后》。但,说老实的,我最喜欢第三章的标题,《滚开》。太文艺有意思么?你想说什么?就说么。不说,就写诗告诉我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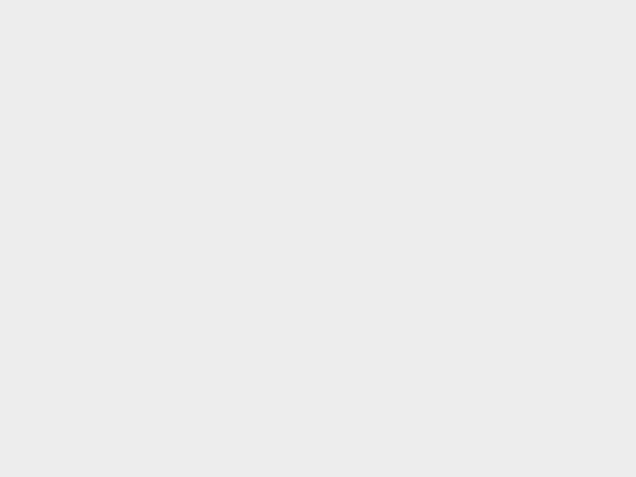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我写诗,设计,艺术,作曲,摄影,绘画,旅行,文艺。如今快三十了,回想回去,我TMD为什么要搞这些?好像在我认识我的第一个女友之前,我是一个《星际争霸》超级高手,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后来我都会了⋯⋯好像都是源于,我看到我第一任女友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嘿,那個誰啊,快來殺我吧。不要怕麽,法律有什麽用?
痛快要在自己掌握。”
然后,我爱上了她。
后来,我什么都会了。
人 有时候 就是有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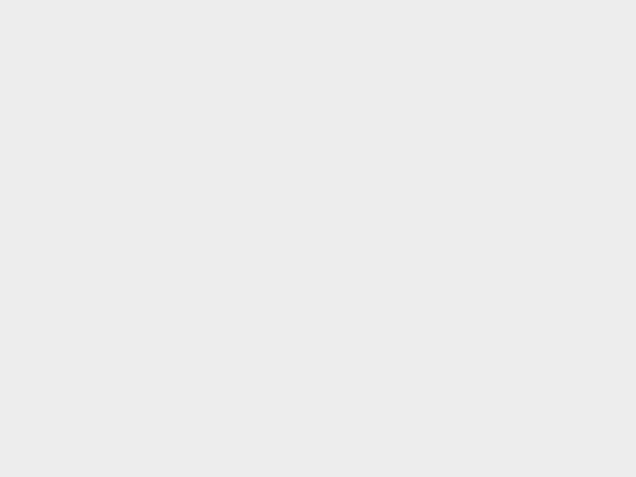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有很多从前的诗歌。我既然用10年来写它们,我也会继续,用10年的时候,来作曲,把她们全部唱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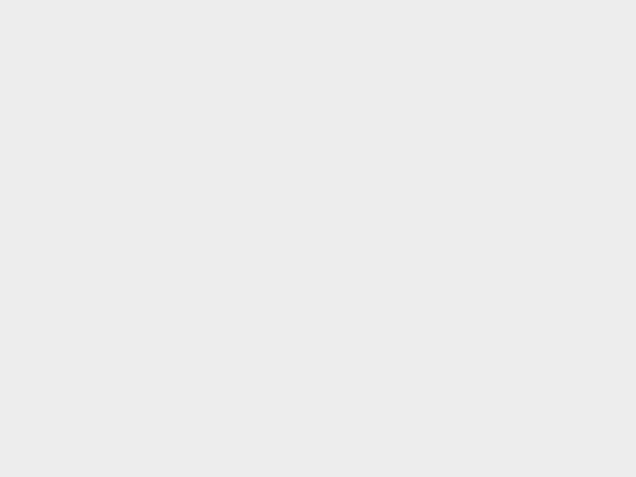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青春来作诗 只是 你未必把她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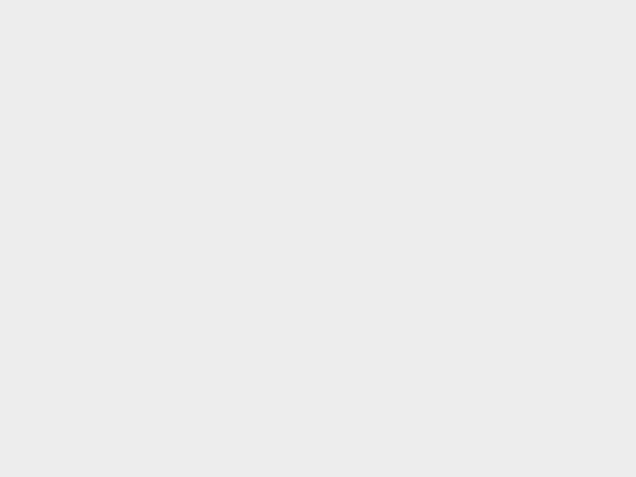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诗歌集的用纸,采用这种类似花岗岩的风格。坚实,砖灰,沉旧,而有我要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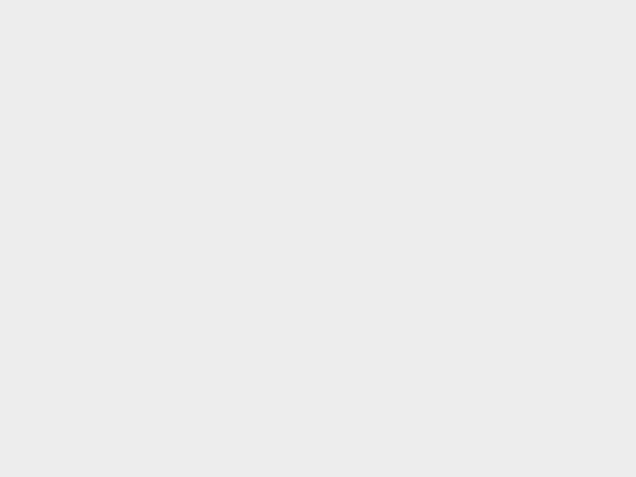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在书的装裱设计,很多细节我都设计过了,譬如书中缝用金漆色,内贴也用金漆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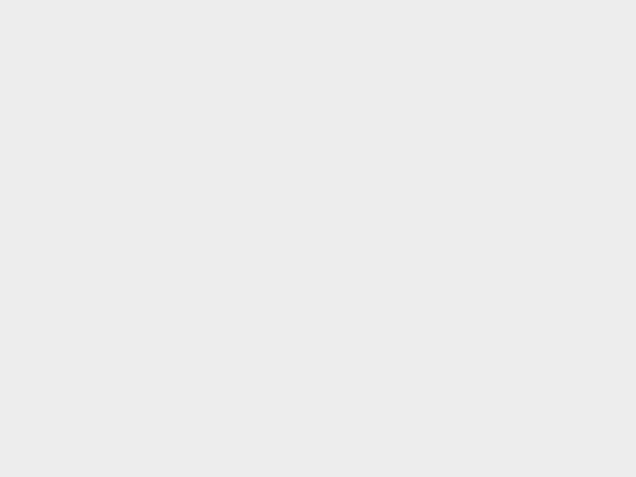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花”字 自从那年在厦大西村租了简单的公寓,避世般的生活,画出来后,就从来没改过。因为,那段岁月太安静了,这种安静而生的作品,是没有必要修缮的,她有我认同的,完美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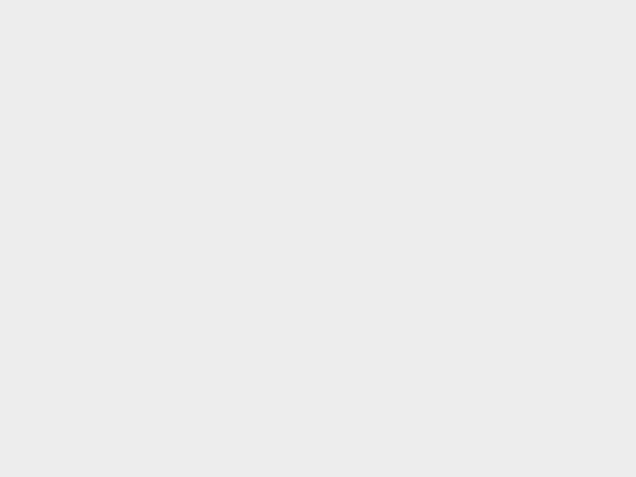
最后想说的是,第九章的题标。“若妳撞見二零零五年的我,記得代我獻上一吻,因為妳這輩子不會有機會再愛上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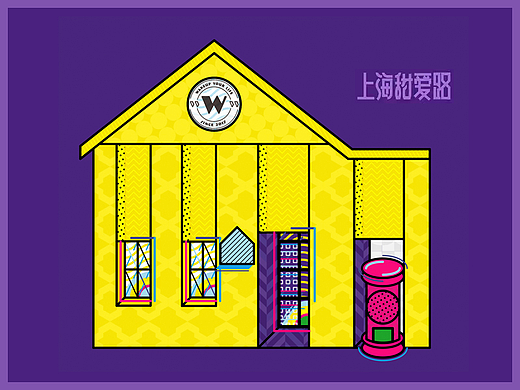






























![ZAOV|各[苹]本事](https://img.zcool.cn/community/68d247ffa534901h5u6ly05445.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w_520,h_390,limit_1/auto-orient,1/sharpen,100/quality,q_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