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间地带
最近读了《在中间地带》一书,摘录一段分享
《在中间地带》起名于我和一些密友之间谈论我们这些游子的处境的对话。在中间地带,有点两头不靠岸的意味,适合于用来为“无家可归” 的尴尬处境作自我解嘲式的辩解。但是,最终,这个说法体现的确实是我一向对于自我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的定位。近二十多年来,我离开“故土”在“海外”生活和工作,自然是处于一种游离变动的状况。从中国到法国,再到美国定居,再加上时常地奔走于世界各地,看来没有比在中间地带更形象的形容了。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其实远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就认定,一个当代的公民,必须是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批判性的见证者,并需要身体力行地为自己的社会和时代提供解构其各种本质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之类正是其登峰造极的极端化意识形态表现,而独裁和法西斯乃是其行动的方式)的精神束缚的想象和方案,以使得每一个个体能够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世界公民,正是因为如此,我,应该说还有我的志同道合者,或者说我们,才会去选择艺术、文学、哲学以及各种研究社会、历史和人文的工作。把自己放在一个与为(广义上的)官方所认定并且为权力体制所确立的观念和价值保持“批判的距离”的立场上不仅是一种专业上的必要,同时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生活抉择。因此,要不违心地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想象、开拓并且坚守我们的中间地带,一个在一切确定性、本质主义及其权力体系之外的第三空间。
生存于中间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第三国,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的彻底改变:永远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之间迁移——不论是物理上的位移还是精神上的天马行空,由此而铸成的身份注定是多重的、复杂的、混血的;既是全球的又是地方的,既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并且不断地衍生新的内容和实质,进而影响所到之处的社会现实的变化。简言之,这体现了所谓与“全球一体化(同质化,英文的globalisation)”相对的,以多元化为前提的“世界化(法文的mondialisation)”的精义。即在迁移于不同国度和文化之间,以及在与之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在制造种种新的现实演变的方案和实验,由此衍生出新的现实本身,亦即制造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全球性的,也是多元共存的,并且是不断变动和更新的。今天真正有价值的时代产物,包括艺术、文学、哲学和其他领域的创作,其实在根本上都体现着这种混血和过渡的性质。中间地带,正是创造的乐土。
作为一个以艺术、文化评论和展览策划为主要专业活动的写作者,我认定,立足于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对时事和历史保持距离,是我思考和实践的起点。同时,无独有偶,我生活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里,一切的思维、想象和交流都是透过“他人的”语言来进行的,无意中,“他人的”语言已然变成了我的新母语。但是这种新母语永远是借来的语言,不可能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原来的母语(其实,我的母语是哪一个?粤语还是普通话?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命题)也因为时代和社会交流方式的变化而“与时共进”了,时常令我无所适从,最终我只好在一种语言的中间地带里讨生活:用非母语——英语和法语——来写作。 无可否认,这种选择是有着严重缺陷的:无法真正精到地把握该语言的文学和诗意的精髓。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与“他人”不断交流和翻译的过程,我们可以在理解、误解“他人”和与之谈判、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和发明新的意义。实际上,这体现的几乎是每一个人在当今时代的全球化生活、思想和表达的最真实的状况。也许,关于我们时代的大量文化、艺术、社会和政治的课题,以其本身固有的混血性质而言,使用不纯粹的非母语可能是最为合适的方式。如同众多学者所主张的,文化之间的翻译从来都是人类文化历史进展的动力和文化存在的根本方式,认同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尤其重要。这是一个不同的全球化观念互相对峙和争夺的时代,各种独裁的强权体系试图以或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颁令的大一统官方语言,或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以消费主义为目的的、传媒式的、奇观式的(spectacular)的、把语义简化到“品牌化”(branding)地步的“普通话”,来对每一个自由和智慧的个人实行洗脑,以使整个社会彻底奴化为服务于其利益的工具。与此相对,越来越多的个人和集体正在觉醒过来,坚守语言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以至混血性,以多元化来抗衡大一统的霸权。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必须发动我们的想象力,创造我们中间地带的语言,游弋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尤其是各种文化的边缘和另类的空间和状态之间,以语意的不稳定性和开放性来拒绝被任何主流的强权控制——拒绝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语言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不是不许别人说话,而是强迫语言的使用者按规定的方式和语意去说话。中间地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建立这种拒绝被奴化的语言乌托邦。换言之,这也引导我们去想象开放和自由的政治乌托邦。
巴特提出文学通过与语言捉迷藏般的躲躲闪闪,运用对语言固有形式结构施展“骗术”的把戏来从语言的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文学的不可捉摸和多元多变,特别是其自成一体的中间地带或者第三空间式的地位,有力地体现着一种彻底的自由。艺术作为不可言说的第三空间,一个永远需要贴近但永远无法用文字语言翻译的中间地带,而描述和传达这种中间地带的涵义和价值的语言——艺术评论的语言,自然也是这个中间地带的一个部分。正是这样的语言“把戏”指向着我们智慧和心灵的自我解放之道。
今天,这本以英文出版的文集得以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实际上又是在本来就混杂和复杂的表达上加上了一层新的模糊性和不可避免的误解。但是,这也给予了作为原作者的我一个和使用中文,或者说至少是我母语的一个部分(普通话或国语)的朋友们进行交流,以至接受他们评判的一个机会。同时也算是给予多年来鼎力支持我而又无从阅读外文的父母、亲友和师长学友们的一个小小的交代。最后,这也可以视为我工作的一个新的中间地带吧! 为此,我特别要感谢促成此事的、与我共事多年或者新近结识的“战友”们:余小蕙作为原书的编辑,欧宁作为原书的“共谋”(策划、设计和中文版的发起者),艾华莲(Evelyne Jouanno)、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杰罗姆?桑斯(Jér?me Sans)、高明潞、卡罗林?特伊(Carolee Thea)、沃特?戴维茨(Wouter Davidts)和泰勒?凡迈尔海格(Tijl Vanmeirhaeghe)、安妮特?巴尔克玛(Annette W. Balkema) 和汉克?斯拉格(Henk Slager)作为合作者, 李如一、翁笑雨和周伟驰作为译者,董冰峰作为最终促成中文版出版的“媒人”;同样重要的是中文版出版者蜜蜂出版公司的张业宏、周凌及其同事,英文原版出版者Timezone 8 (东八时区)的罗伯特 ? 伯纳欧(Robert Bernell)和他的同事,以及不一一细列的各篇文章的原出版者。当然,我不能忘记多年来给予我精神的养料和灵感的艺术家和各位同行。最后,我最深切的感激要给予我的生活和精神的最亲爱的伴侣和支持:我的妻子艾华莲和我的女儿Kim(仲仪)。
中间地带就是我的,也许还有你的,或者说,我们的,永远的生存之地……
摘选自《在中间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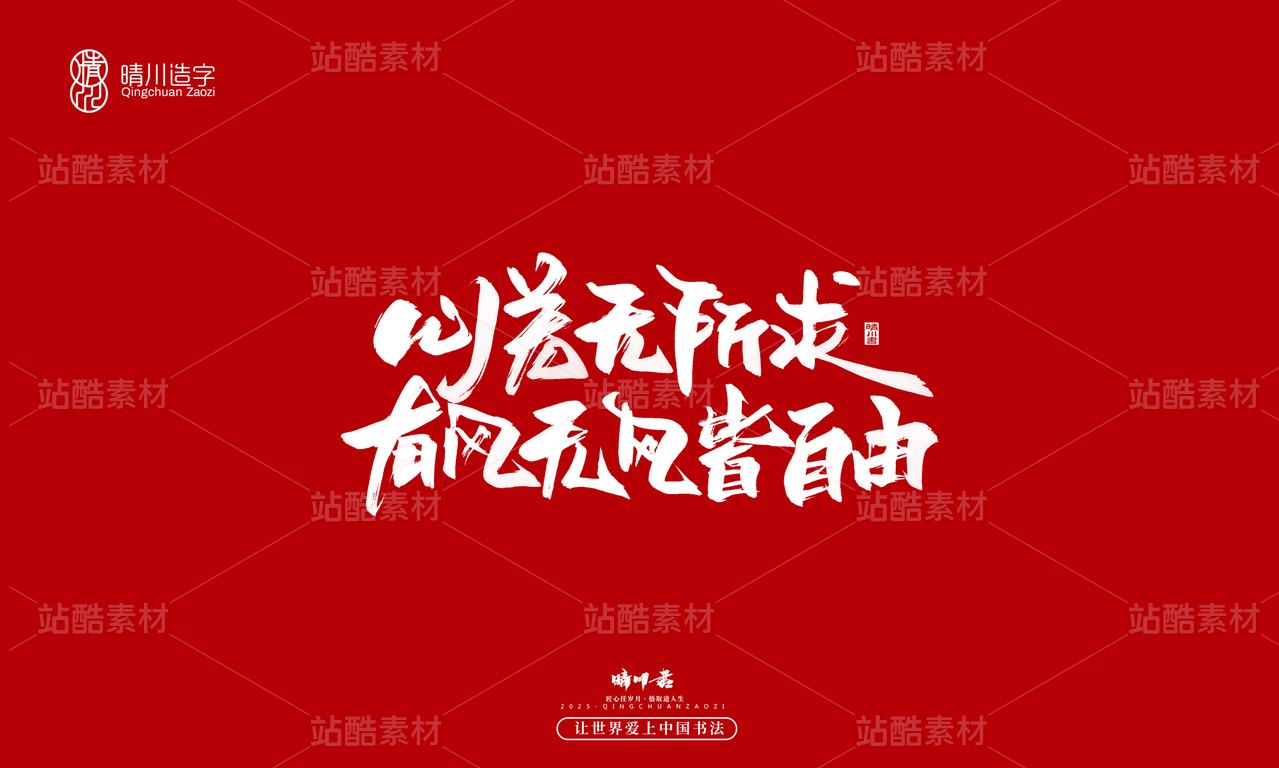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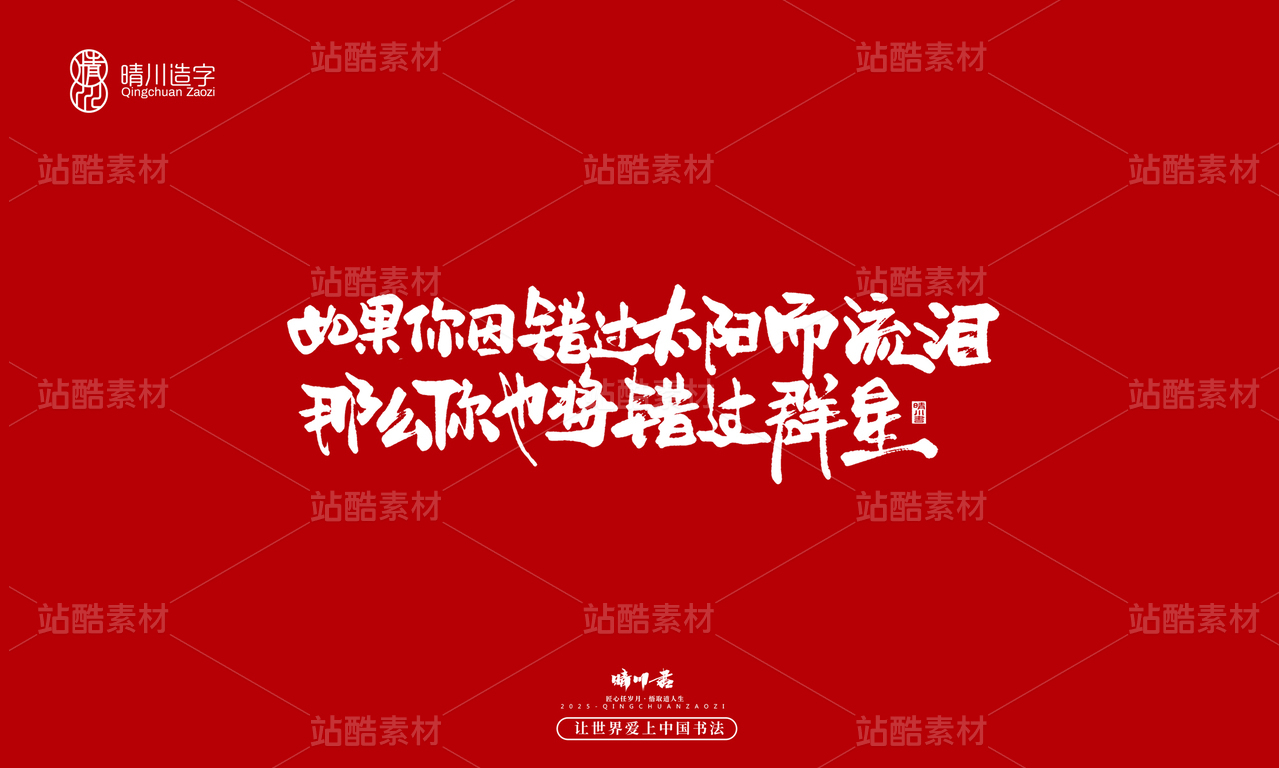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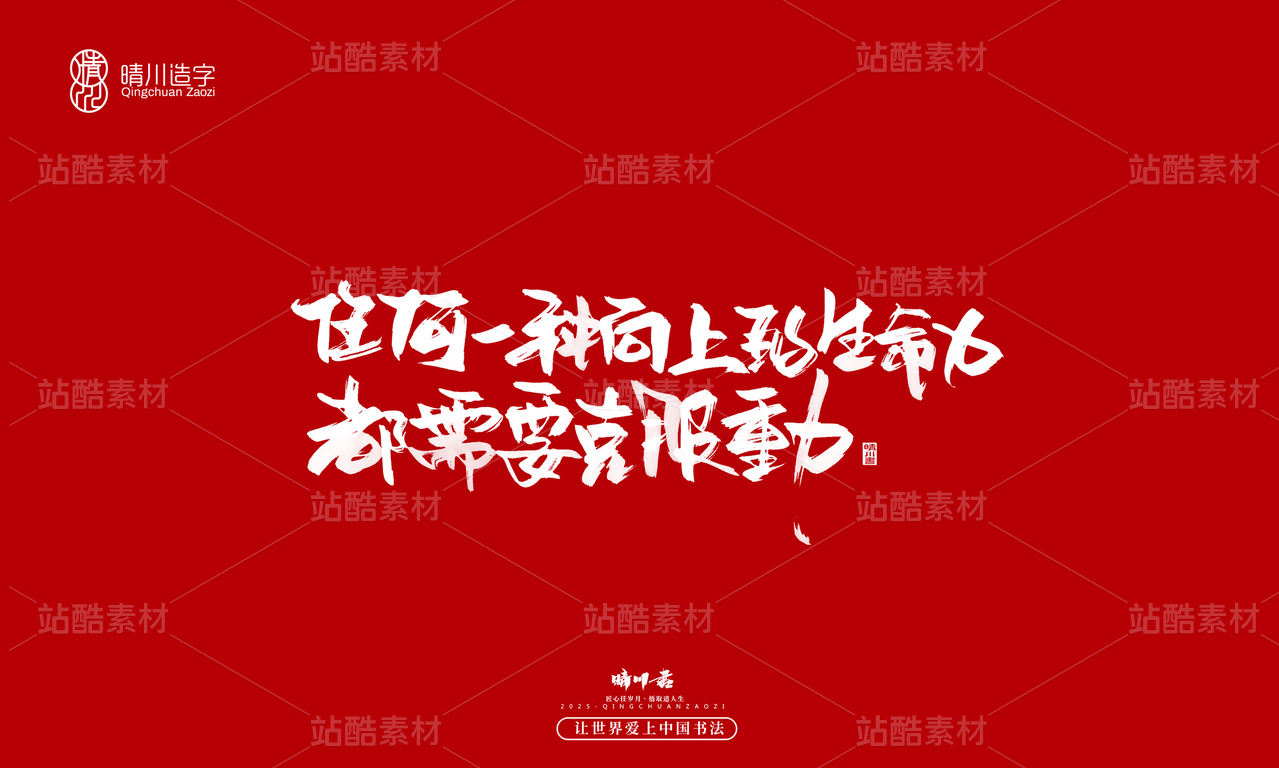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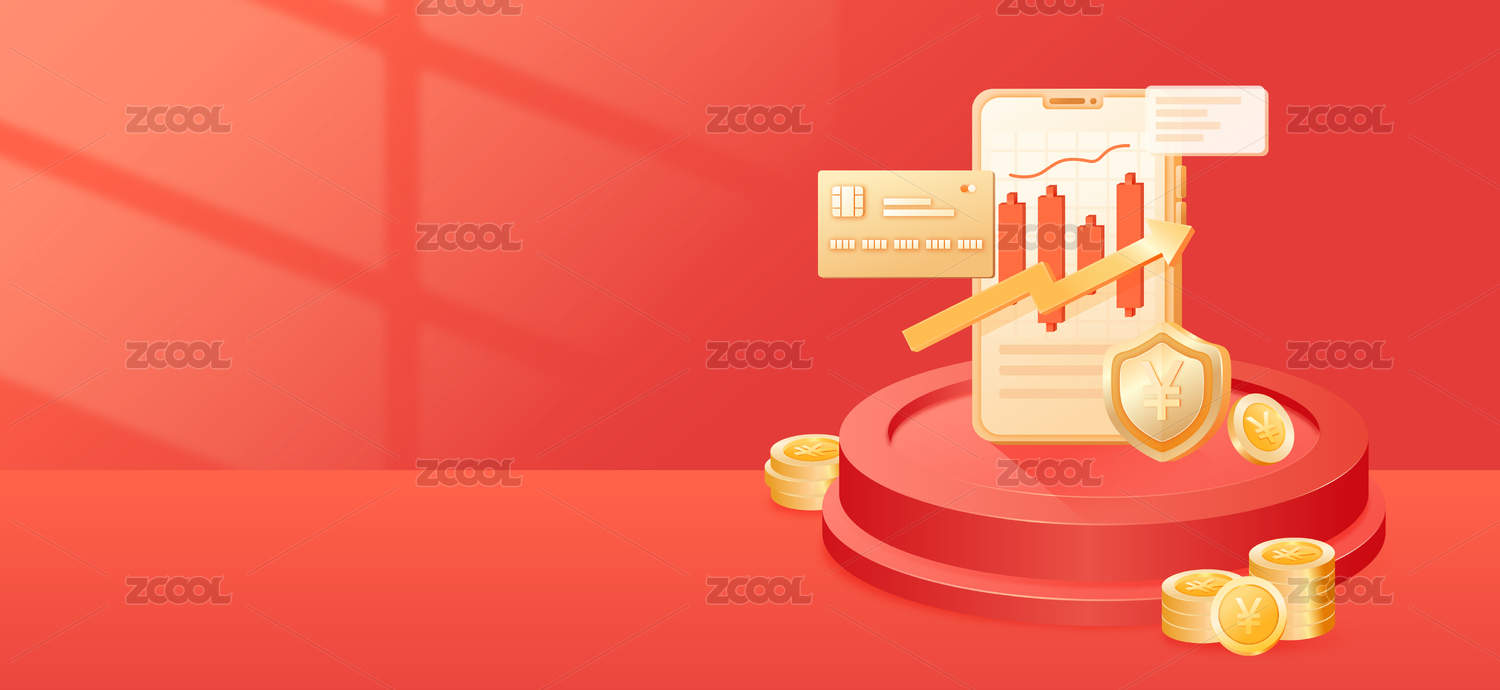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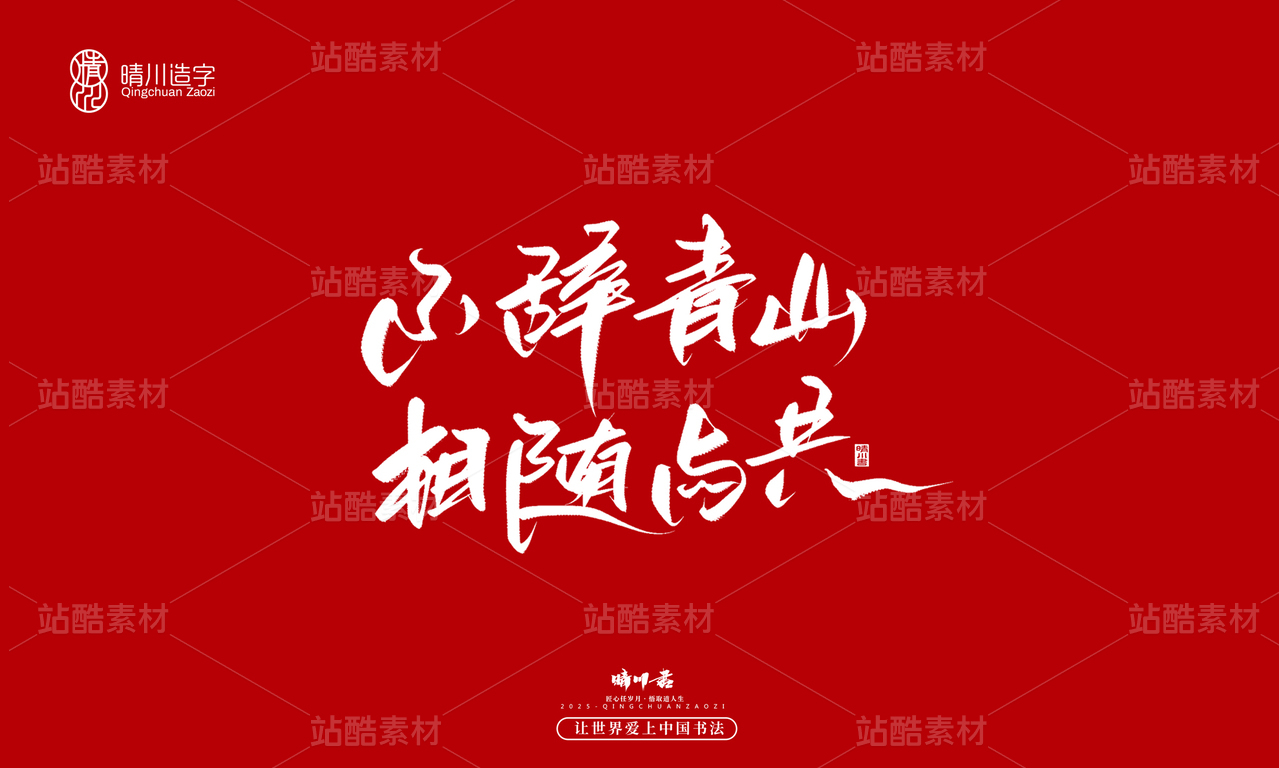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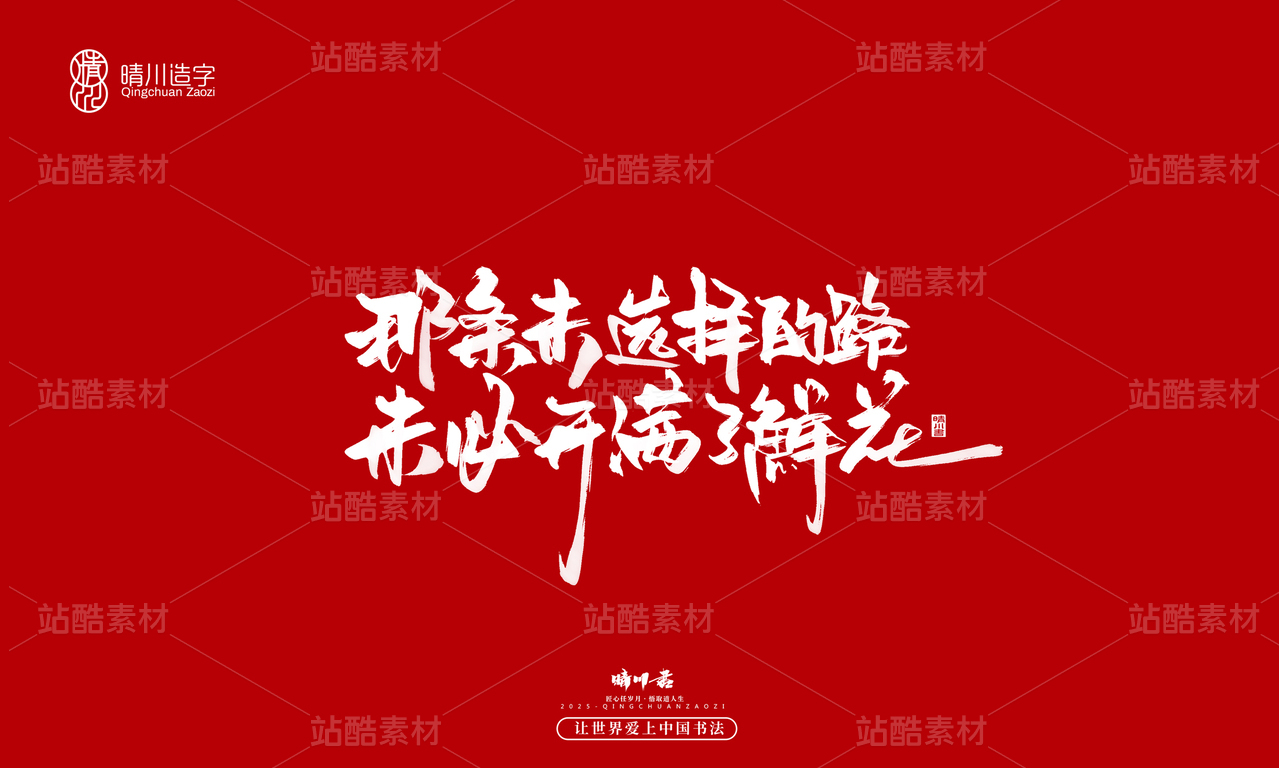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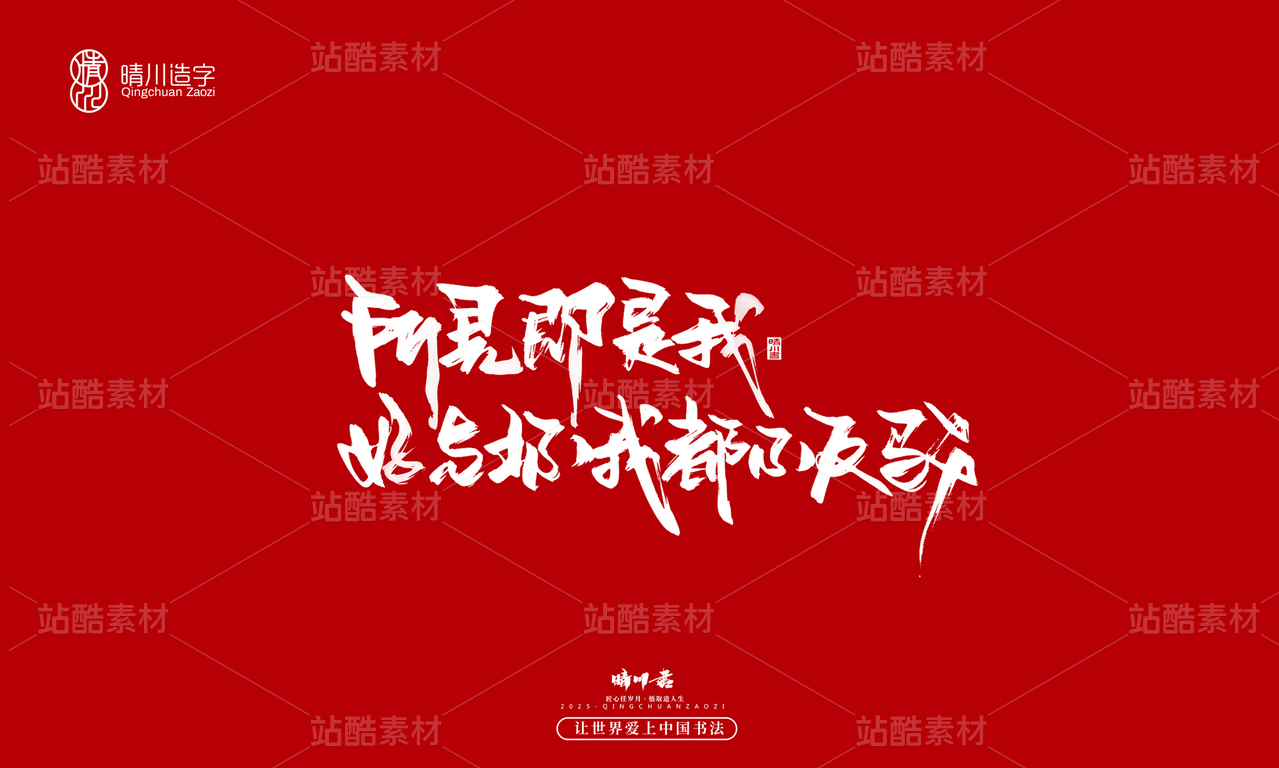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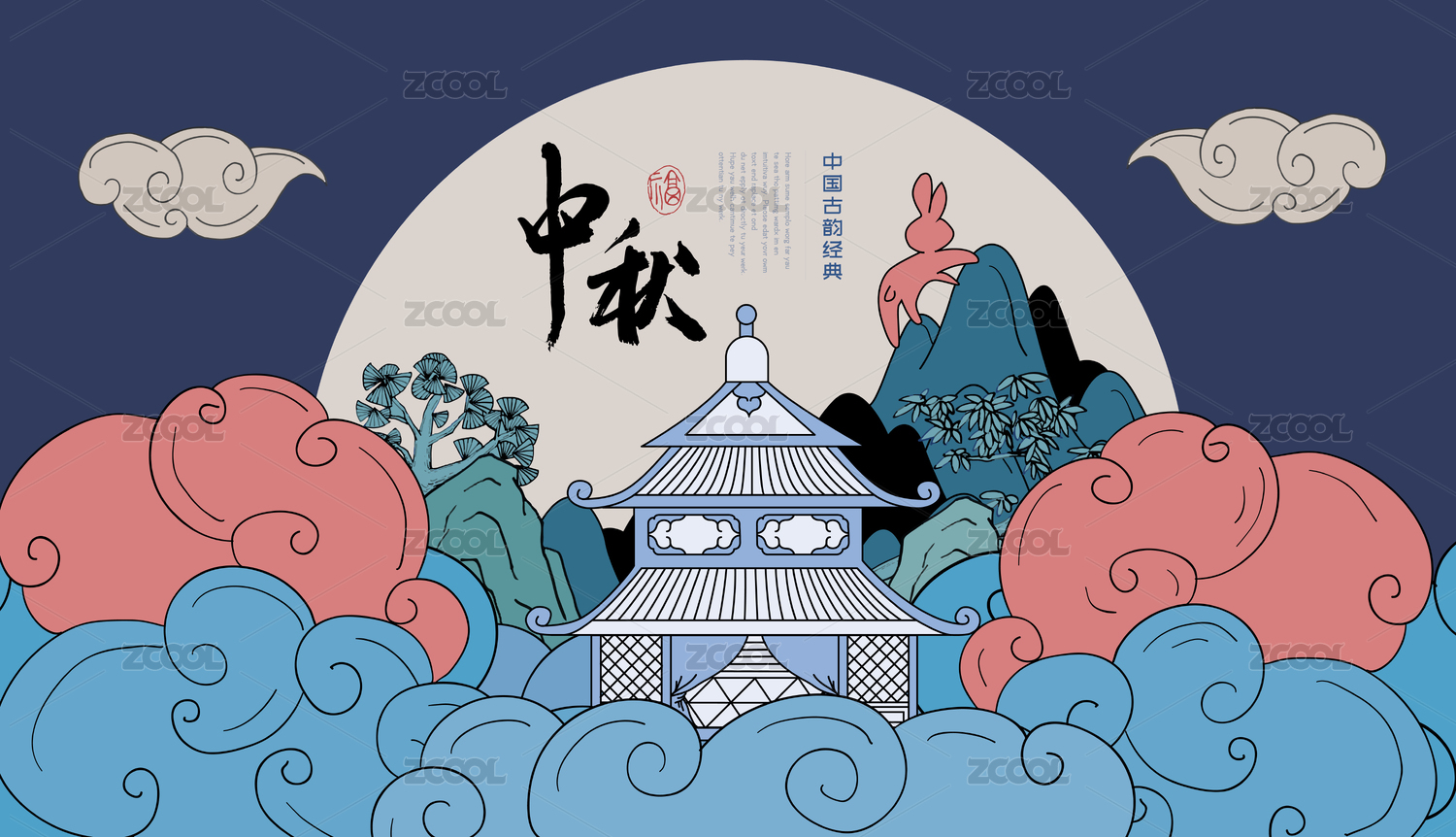




![AIGC助力电商视觉×头盔系列AI生成 [动态化探索实践]](https://img.zcool.cn/community/68e8da720067cv09d9quve1777.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w_520,h_390,limit_1/auto-orient,1/sharpen,100/quality,q_80)








